笔趣阁>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55章(第3页)
第155章(第3页)
>唯有一愿:见兄最后一面,共饮浊酒一杯,谈尽平生志业。
>此非国事,乃私情;非君臣,乃故人。”
牛金读罢,闭目良久。终于点头:“我去。”
启程那日,全境百姓相送十里。孩童捧来新收的稻米,老人献上亲手编织的草鞋。牛金一一收下,却在临行前将所有礼物分赠贫户。
他骑马北上,不再带斧,不再披甲,只背一只药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布袍。
抵达五丈原时,秋叶纷飞。营帐连绵,旌旗半卷。诸葛亮扶病出迎,两人执手无言,唯有泪光盈眶。
夜宿帐中,篝火微明。二人对坐饮酒,一如当年隆中月下。
诸葛笑道:“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你在田里锄草,我说你是隐士,你说你是农夫。”
牛金点头:“我说,锄头比羽扇实在。”
诸葛叹息:“如今我才明白,你才是真正的治国之人。我一生运筹帷幄,却常忽略最根本的事??土地与人心。”
“你也做得很好。”牛金轻声道,“若无你支撑大局,我的田早就被战火烧成了灰。”
翌日,诸葛亮强撑病体,召集诸将,当众宣布:“自今日起,南中政务全权委托牛金,代行丞相监南中事,节制七十二部,便宜行事。”
众将虽惊,却无人敢言反对。皆知此人虽无官爵,实有经纬天地之功。
七日后,牛金告别。临行前,诸葛亮握着他手,气息微弱:“替我看着这江山……别让它垮了。”
“我会的。”牛金答,“只要你种下的信念还在,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归途漫漫。行至巴郡,忽闻噩耗:诸葛亮卒于五丈原,享年五十四。
牛金立于江畔,面北而跪,久久不起。江水滔滔,仿佛载走了那个属于智者与理想的年代。
他回到南中,未发一言,只是默默走进“守心书院”,在墙上添了最后一行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犁,但土地永远需要耕者。”**
此后十年,牛金年岁渐高,步履愈加蹒跚。但他仍坚持每月巡视各村,检查学堂、粮仓、堤坝。每逢春耕秋收,必亲执犁耙,带头下田。
八十岁那年春天,他病倒了。卧床三月,不肯服药,只说:“该走的时候,何必强留?”
临终前一日,他要求家人扶他到田边。正值插秧时节,孩童们正在唱《千字文》。
他听着听着,嘴角浮起笑意。
“把我那把斧头拿来。”他说。
家人取来斧头,已多年未用,刃口却依然锋利。
他轻轻抚摸,喃喃道:“它陪我杀过敌,也劈过柴,还开过渠……很好。”
片刻后,他又说:“把我葬在最初那块公田旁边。不要碑,不要名,只要一?黄土就行。”
众人含泪应允。
次日凌晨,鸡鸣三声,牛金安然离世,享年八十有一。
葬礼那日,万里无云。七十二部百姓自发前来,每人带来一捧新土、一株稻苗,围成圆形坟茔。坟前不立碑石,唯有一把铁斧深深插入大地,如同一面旗帜。
从此以后,每年春耕,农人都会在那把斧旁放下一束稻穗。冬至之夜,孩童们会围着它朗诵《牛公言行录》。
许多年后,有个外国使节路过南中,见此情景,问:“这是哪位帝王的陵墓?”
当地人摇头:“不是帝王。是个种田的将军。”
使节愕然:“种田之人,也能受此尊崇?”
老农指着眼前万亩良田,淡淡道:“你看这片地,哪一寸不是他唤醒的?你看这些孩子,哪一个不是他教化的?你说,他该不该被记住?”
使节默然良久,躬身一拜。
春风拂过,稻浪起伏,仿佛大地在呼吸。那把斧头依旧挺立,锈迹斑斑,却从未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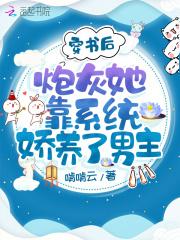
![边疆来了个娇媳妇[年代]](/img/467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