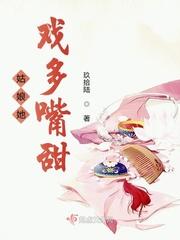笔趣阁>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57章 丧钟为谁而鸣(第2页)
第157章 丧钟为谁而鸣(第2页)
他没有答案,于是下山回书院,召集所有“边塾”精英、守耕队长、乡议代表,共三百余人,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议政”。
会议持续七日。有人主张闭关自守:“南中好不容易太平,岂能再卷入战祸?”
有人痛斥苟安:“若蜀汉覆灭,魏国铁骑南下,谁能独善其身?”
更有青年将领激昂陈词:“我辈习武多年,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保家卫国!请允我率义耕军北上勤王!”
争论激烈,几近撕裂。最后,孟琰起身,手中捧出那把曾埋于牛金墓前的铁斧。
“这把斧头,砍过敌人的头颅,劈过倒塌的房梁,开过千里的水渠。”他声音平静,“但它最重的一击,是从没落下过??因为老师教会我们,出手之前,必须想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为何而战?
第二,谁来承担代价?
第三,打赢之后,百姓能否吃得上饭?”
全场寂静。
“魏国若来,我们当然要战。”孟琰环视众人,“但我们现在支持姜维,并非盲目出兵,而是以‘共耕制’为根基,建立‘战时互助联盟’??南中不出一兵一卒,但每年调粮十万石,派出工匠五百,协助修筑防线、整修道路、培训士卒。同时开放商路,允许军需物资免税通行。”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我们不争一时胜负,而要确保这场战争不会拖垮民生。若朝廷征发无度,我们就以‘谏议录’弹劾;若官员克扣军粮,我们就以‘乡议会’曝光;若百姓苦于徭役,我们就以‘互助社’代偿。”
众人恍然大悟。这才是牛金留下的真正遗产??不是武力,而是制度的力量。
决议通过当日,南中发布《告天下书》,全文仅三百字,却震动朝野:
>“南中百姓,不忘先贤之志。
>牛公教我耕田,亦教我明义。
>今魏患复起,我岂敢自保一方?
>粟可输,工可遣,道可行,唯兵不出。
>非怯也,实恐一旦启衅,田园尽毁,书声断绝。
>愿以粮为箭,以渠为垒,以民智为甲,共守汉祚。”
姜维得讯,抚信长叹:“牛公虽逝,其神犹存。南中有此屏障,吾可安心北伐矣。”
自此,南中成为蜀汉最后的粮仓与精神灯塔。每逢战事吃紧,总有无数百姓自愿捐粮、织布、制药。守心书院每年选派百名优秀学子赴前线担任“军政参事”,负责监督后勤、调解军民矛盾、记录战地实情。
十年光阴荏苒。司马昭篡魏称帝,改国号为晋,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蜀汉危在旦夕。
景耀六年冬,成都陷落前夕,刘禅派人急召孟琰入朝,欲举国托付。
孟琰未去。他在守心书院墙上写下最后一句话:
>**“国可亡,种不能断。”**
然后下令焚毁所有官府档案,只保留《耕贤榜》《谏议录》《乡议会纪要》三类文书,秘密藏于山洞之中。又命妇孺老弱迁入深山,青壮留守城池,准备迎接最后的风暴。
晋军入境之日,孟琰白衣素冠,手捧牛金遗像,率七十二部首领出城十里相迎。
晋将邓艾见状,冷笑:“尔等既降,尚敢列队成阵?”
孟琰平静答道:“我们不是投降,是交还土地。这片田,是我们一锄一锹开出来的;这条渠,是我们一代一代修下去的。今天你们拿走政权,但只要还有人在插秧、在读书、在说真话,南中就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人。”
邓艾沉默良久,终令军队绕城而过,不扰民居,不禁讲学。
数年后,一名晋朝刺史巡视南中,惊讶发现:这里竟无一座帝王庙宇,却处处可见小小的“守心亭”,亭中供奉一把生锈的铁斧,旁边刻着孩子们稚嫩的字迹:“谢谢牛爷爷让我们吃饱饭。”
他问当地县令:“此地百姓为何如此敬重一个老农?”
县令微笑:“因为他们知道,真正养活他们的,从来不是皇帝的诏书,而是春天的那一犁土。”
春风又起,稻浪滚滚。那把斧头依然立在田边,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着岁月流转,也见证着一种信念的延续??
那是关于土地、人心与文明的漫长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