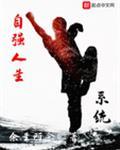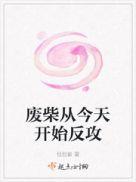笔趣阁>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59章 刘辩刘协附上洛阳皇宫地图(第2页)
第159章 刘辩刘协附上洛阳皇宫地图(第2页)
阿?亲赴疫区查看。她未戴面巾,亦未避嫌,一一探视病人,询问症状,记录病情发展。归来后,立即召集医者、工匠与判议官共商对策。
“这不是瘴疠,也不是寻常伤寒,”一位曾在交州行医的老大夫皱眉道,“传染极快,尤害体弱者。我怀疑是从北方逃难者身上带来的新疾。”
有人立刻建议:“封锁疫区,禁止出入,待其自灭。”
阿?摇头:“不行。那里住着三百多口人,大多是流民安置户。他们刚有了田、有了家,我们怎能弃之不顾?再说,病毒不认户籍,今日封村,明日便会传到别处。”
最终,会议决定启动“防疫共治机制”:第一,设立隔离区与健康区,由志愿者轮班值守,提供饮食医药;第二,征用废弃窑厂改建临时病房,屋顶开窗通风,地面铺石灰消毒;第三,发动妇女纺织麻布口罩,儿童收集草药熬制汤剂;第四,每日傍晚敲钟通报疫情进展,确保信息透明。
最令人震撼的是,阿?宣布:“凡参与防疫者,无论生死,皆录入《义民录》,子孙三代享减免劳役之权。若有牺牲,抚恤金加倍,子女免费入学至成年。”
命令下达当晚,报名志愿者超过两千人。有医生徒步百里赶来支援,有工匠彻夜赶制木床与药架,更有数十名曾受救助的流民跪在守心堂前,恳求前往一线:“我们活到现在,全靠南中收留。如今轮到我们回报了。”
一个月后,疫情终于遏制。死亡人数定格在四十七人,远低于预估。而更宝贵的是,这场灾难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次年春天,《南中防疫条例》正式颁布,成为第一部由民间自治政权制定的系统性卫生法规。
十年后的某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重返南中。他是当年被贬交趾的张俭之子,少时离乡,半生漂泊,如今听闻故土安宁,特来寻根。当他走进义州集市,看见男女老少排队领取疫苗接种凭证,孩童在广场上表演防疫情景剧,墙上张贴着“勤洗手、戴口罩、不聚集”的图画告示时,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临终前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眼见到南中真正站起来。”他对接待他的年轻判议官说道,“现在我知道了,它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走出了自己的路。”
那人微笑:“我们不谈‘站起来’,我们只谈‘不倒下’。只要还有人记得同心堰的碑文,还有人愿意为陌生人冒一次险,这片土地就不会倒。”
冬去春来,岁月如流。景熙四十年,阿勒泰寿终正寝,享年一百零三岁。临终前,他召集所有判议官,最后一次抚摸铁斧。
“我见过战火,也见过饥荒;见过背叛,也见过奇迹。”他气息微弱,眼神却明亮如星,“但我最欣慰的,不是我们打败了多少敌人,而是我们始终没有变成他们。我们没有城墙,因为我们不需要防备自己人;我们没有监狱,因为犯错之人愿意改过;我们没有皇帝,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他闭眼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孩子们……继续相信那把斧头。”
葬礼那天,七十二部代表齐聚守心堂。没有哀乐,没有跪拜,只有thousands人齐声诵读《约法三章》:
>“一曰共耕,不得私占;
>二曰共议,不得专断;
>三曰共责,不得逃避。”
诵毕,众人将一??泥土撒入墓穴,每一捧都来自不同村落,象征着七十二部的合一。
此后数年,南中依旧平静。没有战争,也没有英雄史诗。但它的影响却如地下水脉,悄然渗透四方。滇西的濮僚部落仿效轮值亭制度,选出首位女酋长;黔北的夜郎遗民重建议会,废除血祭习俗;就连远在岭南的俚人山寨,也开始用木刻记事、公投决策。
某日清晨,一名渔夫在红水河畔打捞起一块残破陶片,上面隐约可见几个古篆:“仁政在野,不在朝;民心所向,即为正统。”
消息传开,无人刻意宣扬,但这句话却被悄悄刻在了多地学堂的墙壁上。
又是一年春耕时节。山坡上,犁铧翻动新土,几名少年正在测量田埂间距,准备绘制新的灌溉图。远处传来琅琅书声,那是守心书院的新课:
>“权力生于信任,毁于垄断;
>规则贵在执行,不在书写;
>文明不在庙堂之高,而在阡陌之间的一碗稀粥、一句承诺。”
天空湛蓝,白云悠悠。铁斧静静矗立,影子斜落在freshlytilled的土地上,仿佛一道连接过去的刻度线。风吹过稻田,掀起层层绿浪,如同无数双手,在无声地传递着同一个信念:
宁做一寸土之耕夫,不为千里江山之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