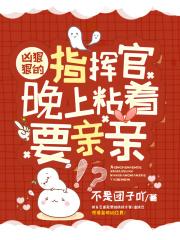笔趣阁>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68章 她在求死(第3页)
第168章 她在求死(第3页)
冬去春来,南中迎来新一轮“毕业墙”投票。今年争论激烈,有提议刻“知识即力量”,有主张写“团结就是长城”,最终胜出的,竟是一个聋哑少年用手语表达的话,由老师代书:
>“听不见的人,也能发出光。”
石匠精心镌刻完毕,校长率全体师生静默三分钟,随后齐声诵读南中誓词:
>“我们不求天降圣君,
>只愿人人能思、能问、能言、能行。
>我们不信宿命,
>只信今日所做之事,
>决定明日之世道。”
同年夏,长江汛期平稳度过。李昭带领学生完成“千桥计划”最后一桥??问字桥竣工仪式上,没有官员致辞,只有五十名村民轮流登台,讲述自己如何通过议事会决定桥梁走向、预算分配与维护轮值。最后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说:“我爸原来总打我妈,后来参加了议事亭,学会了‘尊重’这个词,现在……现在他给我梳头。”
全场寂静,继而掌声如雷。
阿?站在人群中,默默流泪。
当晚,他独坐守心堂,翻阅各地送来的“民间新规”:凉州村规写明“女子可继承田产”;巴郡乡约规定“议事需半数女性参与”;就连远在辽东的渔村,也自发制定《海权共约》,明确“捕捞限额由全体渔民公投决定”。
他提笔写下年度总结呈报朝廷:
>“所谓治国,不在令行禁止,
>而在民心自明。
>今日之南中,非我一人之功,
>乃千万百姓在井台、在田埂、在桥头、在灯下,
>一字一句,商量出来的活路。
>民思所向,金石为开。
>臣不敢居功,唯愿此火不熄,
>照彻千古长夜。”
奏章发出次日,信鸢再次降临肩头。这次它不再来自远方,而是从南中腹地最偏远的一个山村飞来。尾翼小字变了:
>“我们也看见了。”
阿?笑了。他蘸墨添上最后一句:
>“那就继续飞吧,
>直到再也没有人需要问:
>‘我能相信谁?’
>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每一寸土地上,
>在每一个抬起头的人来说出‘我’的那个瞬间。”
信鸢振翅,冲入云霄。
山下,新一批孩童正在练习写字。老师问:“你们长大想做什么?”
有的说想造桥,有的说想治病,有个瘦弱男孩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当第一个从南中走到大秦的信使!”
全班哄笑,老师却认真点头:“好。那你得先学会写信。”
男孩坐下,咬着笔杆,一笔一画,写下人生第一句话:
“亲爱的远方朋友,你好,我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