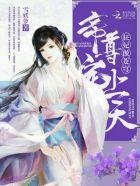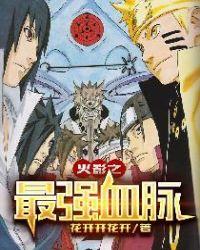笔趣阁>淮阴县主·邯郸道 > 自是风尘外物上(第2页)
自是风尘外物上(第2页)
“县主出身儒学世家,在此堂前,应以桓氏为先。”萧迦叶也客气道,“请。”
桓清与欠身一礼,依言入座。
有人对这个座次顺序颇为满意,“萧氏三代武官,族中无一人精通文墨,为世家高门所不齿,今日看来虽身为兵家子,萧将军却还是知礼之人。”这人说话声不大不小,桓清与刚好听得清清楚楚,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已有几分不耐。
多年来,若非不得不出席的场合,她一向不爱在士族清谈会、宴会上露脸。一是不爱且不善清谈,二是但凡以淮阴县主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眼前,她就不仅仅是桓清与,而是桓相和晋国长公主之女,必得顾及桓家和皇室的颜面。
礼仪、德行,是她给自己设下的禁制,本就无才名,她不能再让自己沦为那些她不屑一顾之人的笑柄。所以哪怕遇小人,也不便撕破脸与之对骂。这种修炼,可以说是清者自清,也可以说是忍气吞声。
她端坐席上,待连云等人布置好茶席,才饮了一杯茶,暗自平复气息。
有人为一举平定北疆的堂堂卫将军萧迦叶辩护,其他士子又说起了袁氏所编的《名士传》,“当朝世家高门均在其列,偏偏没提被封了太尉,位列八公的萧家。萧家门第如何,岂非一目了然?”
身侧,萧迦叶寻常饮茶,寻常语气对桓清与说道:“俭和杜老亦是旧识,我邀他同行,后遭拒绝,说县主应付这种场合十分得心应手。眼下看来确乎如此。”说着,他继续饮茶,低眉道:“几年过去,你已不在意世间评议,很了不起。”
他说的是五年前。
那时,他问过她,会在意世人的喜欢么?
桓清与诚实地答道:在意。
事实上,如今也是在意的。只是学会了掩饰和淡忘。
席间之人,从《名士传》又聊到了如今舆论场上炙手可热的桓俭,提起桓家大公子,人人称赞其文武兼备,风度修然,为当世名士表率!只惜他此番回京以来,深居简出,鲜少在清谈会上露面,令人抱憾。
桓清与听着人群中七嘴八舌的议论,轻声对身侧之人说道:“论得心应手,清与恐怕难望将军项背。”说完,她举杯低眉,掩去了神色,低声抱怨道:“早知今日情形,我也推辞不敢来了。”
萧迦叶见她忽然兜不住露了本相,忍不住笑了一声。
桓清与转头看去,冷峻的少年将军此刻神采飞扬,洒然中另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度。
看了一瞬,她急忙回头。心道,在这个对美貌趋之若鹜,附庸风雅的舆论场里,分明只要迁就时下审美,轻裘缓带,羽扇纶巾,也可收获一批追随者,这人偏要和时风对着干,一身玄色胡装,窄腰紧袖,半分烟云水气也无。
萧迦叶看了看竹林外的车驾,道:“今日的戏,这才开场。”
桓清与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竹林外聚集了许多装饰华贵的车驾。为首一人,衣衫轻薄,高蹬木屐,手执麈尾从马车上下来,其人肤若白雪,貌若春花,风姿特秀,其矫矫不群之态,更令无数人为之倾倒。
桓清与闭了闭眼,心底无声冷笑——今日来此,真是悔不当初!
“你知崔冉今日会出现?”
“不知。”萧迦叶如实回道,“不过我邀俭同行时,他原本一口答应,事后才反悔,那日恰好齐浔也在场。”
这和设计引崔冉现身有何区别?桓清与腹诽道。崔冉在年轻一辈中最早入名士之流,和他手上那柄名贵麈尾一般,清谈会上,信手拂之,便有领袖群伦之意。
齐浔则是士族子弟中掌控舆论的高手,任何小道消息一旦被他知晓,总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传到需要知晓此事的人耳朵里。这是借齐浔之口,让金陵名士们以为桓俭要现身此地,纷纷赶着来和他一较高下。
崔冉足下生风,一路摇着麈尾行至堂前,惹得席间议论不休。他却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眼里,目光淡淡环视一周后,驻足韩子像前,倏忽转身,麈尾横执于胸前,薄唇浅笑。
桓清与察觉到他投来的目光,平视之。
没有一句寒暄,崔冉开口便道:“所谓笨鸟先飞,能在此地偶遇县主,可见县主尚知勤能补拙!此心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