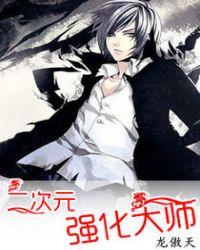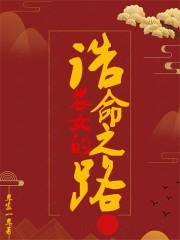笔趣阁>稚御山河 > 第三十三回 民谣惊殿揭苛吏影 诗笺藏讽触龙颜(第2页)
第三十三回 民谣惊殿揭苛吏影 诗笺藏讽触龙颜(第2页)
齐王目光扫过脸色骤变的钱为业,声音愈发沉稳:“这些百姓不敢在杜之贵任时声张,如今他走了,才敢吐实情。本王并非要驳吏部选官之规,只是想问一句——这样的‘政绩’,真配得上扬州刺史之位?真能让江淮百姓安心?”钱为业先是低笑两声,紫袍袖口随抬手动作轻晃,刻意压下心头的慌,面上依旧端着沉稳:“王爷说笑了!您这‘证词’来得蹊跷——杜之贵离城阳不过月余,这些百姓早不吐实情、晚不吐实情,偏等王爷派人去了才开口,难保不是有人暗中挑唆,故意抹黑!”
他上前半步,指尖点了点御案上的纸册:“再说,拓漕渠征劳力,是为了全郡民生,事后也免了当年的赋税;漕粮增收,是因为去年年成好,多缴的粮是为了备荒;至于‘护航费’,不过是商户间的流言——这些事,吏部考课时都有卷宗佐证,怎会是王爷说的‘苛敛扰民’?”
这番话看似有条有理,实则全是模糊说辞:“免赋税”没提免了多少、是否真落到百姓头上,“备荒粮”没说粮囤在哪,“流言”更是直接否定证词。可一旁的周宝奎等人立马附和:“钱大人说得是!百姓不懂政务,难免听风就是雨,哪比得上吏部卷宗详实!”一时间,倒真有几分“证词不可信”的架势。身着深绯色官袍的朱启建快步出班,朝御座躬身行礼后,转头看向齐王,语气带着几分急切的附和:“殿下,臣附议钱尚书!您这证词实在经不起细究——城阳去年拓漕渠,臣曾奉命去巡查,亲眼见官府给劳力发了粮米,虽不算丰厚,却绝非‘不给粮饷’;至于漕粮增收,那是因为当年雨水足,亩产比往年多两成,多缴的粮都入了郡仓,臣还查验过仓廪账簿,字字清晰,何来‘苛敛’之说?”
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殿内官员,声音更响了几分:“再说那些‘诉苦’的百姓,臣听闻其中有几户是当年囤粮被查的粮商亲属,还有因偷税漏税被杜太守处罚过的商户——他们本就对杜太守心存不满,说的话哪能当真?殿下仁慈,心系民生是好事,可若被这些人蒙骗,反倒错怪了实心办事的好官啊!”
这番话看似摆了“巡查经历”“账簿证据”,实则避开了“粮米是否足额发放”“仓廪粮食是否真用于备荒”的核心问题,只拿“百姓身份”做文章,倒也引得几位中层官员悄悄点头,给钱为业添了几分底气。齐王闻言轻笑一声,绯色袍角在阶前扫过,语气里带着几分了然:“看来各位大人,是觉得本王这百姓证词‘不足为信’?”
他话锋陡然一转,抬手从侍从手中接过一卷素笺,扬声道:“可杜之贵离城阳时,百姓‘赠’他的万民伞,总不是本王捏造的吧?伞上还题了首颂诗,诸位大人怕是没细品过其中意味——既然不知,本王便念给大家听听。”
说罢,他展开素笺,声音清朗,一字一句念道:“杜稷安邦赖俊贤,之推避禄美名传。贵以德馨孚众望,万邦臣服颂尧天。民怀惠政思召伯,伞覆黔黎沐舜泉。恭送明公赴江表,贺声满路动山川。”
念完,他将素笺递向内侍,示意呈给向昚与百官传阅,眼底笑意更浓:“这首诗表面是夸杜之贵‘德馨孚众望’,可诸位再细想——‘之推避禄’用的是介子推拒官隐退的典故,杜之贵一心求官,何来‘避禄’?‘思召伯’是百姓感念召公仁政,若他真如各位所说‘实心办事’,百姓何需用先贤反衬?这诗里的讽刺,可比百姓证词直白多了。”
齐王将素笺往御案前一递,声音陡然提了几分,像颗石子砸进平静的湖面:“各位大人皆是饱学之士,诗中藏着的弦外之音,总该比本王看得通透吧?杜之贵若真如吏部说的那般‘勤政爱民’,百姓为何要在‘颂诗’里用‘之推避禄’暗讽?又为何借‘召伯惠政’反衬?他当得起诗里的‘贤人’二字吗?还是说,我朝竟真出了这般‘百姓偷偷写反话称赞’的良善之官?本王倒真是头回见。”
他目光先锁向钱为业,语气带着不容回避的追问:“钱尚书,杜之贵是你力荐的人选,这诗里的深意,你得给大家说说吧?”又转头看向孙幽古,“孙丞相才学卓绝,平日里点评诗文最是精准,今日怎么也该指点指点,这‘万民伞颂诗’到底是夸人,还是藏着别的意思?”最后扫过朱启建与一众官员,“还有朱大人、各位同僚,你们方才为杜之贵辩解时头头是道,如今对着这诗,也该说说看法吧?”
满殿目光瞬间聚焦在孙幽古身上,他这才缓缓放下玉笏,语气淡得没半点波澜:“诗无达诂,百姓题诗或许是真心感念,或许是一时兴起,哪能单凭几句典故就定调?再说万民伞是城阳百姓所赠,杜之贵未必知晓诗中深意——总不能因一首诗的解读有分歧,就否定一个官员的政绩吧?”
这番话看似说了“看法”,实则既没说诗是夸人,也没说诗是讽刺,更没沾“支持杜之贵”或“质疑杜之贵”的边,依旧是不偏不倚的“三不沾”。钱为业见状,忙接过话头:“丞相说得是!诗文解读本就各有不同,怎能拿这个当证据?再说杜之贵已赴扬州,若因此诗小题大做,反倒显得朝堂度量小!”朱启建也连忙附和,殿内又陷入了各执一词的争执,唯独孙幽古,重新端坐在案后,仿佛方才那番话只是随口闲聊,与自己毫无干系。
齐王往前半步,绯色袍角在御阶前扫过,语气带着几分笃定:“钱尚书既说诗文解读各有不同,又说杜之贵配得上扬州之任,那便请尚书大人详解一番——这‘之推避禄’‘思召伯’两句,到底是百姓真心夸赞,还是另有隐情?也好让我等、让陛下都解了惑。若解完惑,真能证明杜之贵功大于过,本王不仅不拦着他赴任,还会亲自向陛下递折,举荐他入中书议事,如何?”
这话堵得钱为业心头一紧,指尖攥着玉笏的力道都变了——他方才只想着用“解读分歧”搪塞,哪料到齐王会逼他当众拆解诗句?满殿官员都是饱学之士,介子推拒禄、召公惠政的典故谁不清楚?若说“百姓用错典故”,显得自己搪塞;若说“是真夸赞”,又与典故原意相悖,只会让人觉得他强词夺理。
钱为业僵在原地,面色渐渐泛白,额角沁出细汗,脑子里飞速翻找着说辞——从《诗经》注解想到前朝诗话,却没一句能圆这个“夸人用反典”的漏洞。约莫一盏茶的功夫,殿内静得能听见烛火噼啪声,他才勉强开口,声音带着几分发紧:“这……这首诗许是城阳百姓没读过多少书,误用了典故也未可知。他们想夸杜之贵‘清廉’,却记错了介子推的故事;想赞他‘爱民’,又只知召公的名声……百姓心意是真的,不过是用词粗疏罢了,当不得真。”
这话刚落,殿内便有几声低低的嗤笑——谁都听得出这是强辩,哪有百姓集体“误用典故”,还把反讽的话编得合辙押韵的?可钱为业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说:“再说……再说杜之贵任内拓漕渠、增岁入,这些实打实的政绩,总比一首用词粗疏的诗可信吧?”
向昚坐在龙椅上,听着满殿“典故”“诗句”的争论,眉头早拧成了疙瘩——他自小不爱读书,哪懂什么“之推避禄”“召公惠政”?眼见众人从吵吵嚷嚷变成“君子论道”,终于忍不住起身,金纹龙袍扫过御案,语气带着几分不耐:“你们到底在说啥?一会儿杜之贵好,一会儿杜之贵坏,又是诗又是证词的,朕听着糊涂!有话不能说直白点?”
齐王连忙上前躬身,刻意放软了语气,用最浅白的话解释:“陛下,是这么回事。臣弟查了城阳的事,百姓说杜之贵在那儿收重粮、征劳力,还欺负商户,可吏部说他是好官,还给他升了扬州刺史。后来杜之贵走时,百姓送了他一把写着诗的伞,表面是夸他,实则是说他跟诗里的好官差远了——就好比有人跟您说‘陛下您真节俭’,转头却指着您满殿的金器笑,一个道理。”
向昚这才恍然大悟,指着御案上的素笺,语气瞬间沉了:“你的意思是,杜之贵是装出来的好官?还骗了吏部?”
“臣弟不敢断言,但百姓的话、诗里的隐情,总不能全是假的。”齐王趁热打铁,“若真让他去了扬州,那地方比城阳富得多,他要是还像从前那样行事,江淮的百姓可就遭罪了,朝廷的脸面也不好看啊!”
向昚转头看向阶下的孙幽古,龙椅扶手被他攥得发紧,语气带着几分依赖:“孙相,齐王说的是这么个意思不?那百姓真是藏着话骂杜之贵?朕读书少听不懂那些弯弯绕,但你是老臣,肯定比朕明白——你说说,齐王这话到底真不真?”
孙幽古心里暗自叫苦:“好端端的争执,怎么又把火烧到我身上?”面上却依旧端着沉稳,躬身回话时语气模棱两可:“陛下,齐王殿下心系民生,查得细致是好事;只是百姓心思最难猜,有的或许是真心感念杜之贵拓漕渠的便利,有的或许是对征粮有怨言,才在诗里藏了些情绪——说是‘全假’不妥,说是‘全真’也未必。”
他顿了顿,又补了句不痛不痒的话:“毕竟城阳之事,有吏部的考课卷宗,有百姓的口头说辞,还有这诗里的隐情,三方各有各的说法。不如让巡按御史再去城阳查一趟,把事情捋顺了,既不冤枉好官,也不委屈百姓,陛下您看如何?”
这番话听着像给了办法,实则还是“三不沾”——没说齐王对,没说吏部错,更没碰“杜之贵是否称职”的核心,只把问题推给了“再查一次”,让向昚觉得有道理,却没从根本上解决争执。
钱为业眼睛一亮,连忙顺着孙幽古的话茬上前半步,紫袍下摆扫过地砖时都带着急切:“陛下!丞相所言极是!巡按御史查案最是公允,定能还杜之贵一个清白!”
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添了几分恳切:“杜之贵在城阳三年,拓漕渠时亲自守在工地半个月,脚都磨破了;漕粮增收后,还拿出三成存粮赈济过周边受灾的村落——这些事吏部卷宗里都有记载,还有乡老的感谢信为证,绝非空穴来风。”
“至于那首诗和百姓说辞,”他刻意放缓语速,像是在替杜之贵辩解,实则在给自己留余地,“许是有人见杜之贵擢升扬州,心生嫉妒,故意在百姓耳边挑唆,又在诗里做了手脚——毕竟杜之贵刚离城阳,若真有那么多民怨,他任内怎么没人告发?偏等他升了官才冒出来这些说法,实在蹊跷啊!”
这番话把“质疑”全推给“有人挑唆”,又搬出“卷宗”“感谢信”撑场面,既保了杜之贵,也间接撇清了自己“选官失察”的嫌疑,听得一旁的朱启建等人连忙附和,殿内的争论又隐隐偏向了“再查再议”的方向。
向昚挠了挠龙袍袖口,脸上带着几分孩童似的困惑,对着齐王直皱眉:“齐王啊,你看丞相和钱尚书都这么说了,还说让巡按再去查,你还有啥好争的?再说杜之贵都当上扬州刺史了,总不能刚任命就撤了吧?”
他顿了顿,又自顾自嘀咕起来,语气里满是直白的天真:“朕觉得吧,要是杜之贵真坏,城阳人早闹起来了,哪能等他走了才说?说不定就是有人看他升了官,故意找茬呢?你要是还不放心,等巡按查完了,是好是坏不就清楚了?现在吵来吵去的,也没个结果,多费劲啊。”
齐王上前一步,绯色袍角在御阶前绷出冷硬弧度,声音里没了先前的平缓,多了几分掷地有声的锐利:“陛下,臣弟若说,方才那些证词、诗句还不够,那这城阳街头传的歌谣,总藏不住假吧?‘一只雀儿往南飞,落在侯爷暖阁西’——这‘雀儿’,可不是真雀,是杜之贵从城阳‘暖乐楼’里赎出的歌女张翠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