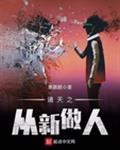笔趣阁>景元七年轶闻 > 第二章 学堂闹事(第2页)
第二章 学堂闹事(第2页)
士农工商,阮家是商户,日子还过得去,却无甚地位。阮老太爷年少时白手起家,历经波折,不知遭了多少冷眼刁难,家业起来后,和别家商户都不同的是,偏要以诗书传家。费尽气力请了好先生建了家学,全家子弟甚至是女孩子都要去家学读书。
别说是春晚城,便是在光州的商贾之中,让家中姑娘也去家塾念四书五经的,只怕也是独一份。因此也颇得了些诗书治家的名声。
也有眼红的,说阮家不过一般商户,连光州大贾之列都还没挤进去,却装腔作势沽名钓誉,还想着让子孙正经走仕途,也是痴心妄想。
不管怎么说,阮家学堂是累年积月教授科考内容的,就连林家的二少爷林深这几年也时不时来听学,向钱先生讨教,深得钱先生欣赏。
学堂这些阮家少爷还小,都还没去参加过童试。阮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秀才公是阮三老爷。
阮三老爷少时聪慧,奋发读书,年不到二十就中了秀才,后来也去考过乡试,连试未中,也就没了心气。阮老太爷便在春晚城活动一番,为三老爷挣了个主簿的位子。自此,阮家也算摸上官路的边了。
有了秀才公的身份,阮三老爷说亲时也自不同一些,三奶奶郑氏是春晚城县学教谕的独生女,育有四姑娘、五姑娘。
按理说,阮家唯一在官面上的人该是家里最重视的,但阮三老爷许是把书读迂了,拿着读书人的矜持劲,在外与人为善帮人办事鲜少收好处,在家里就讲个礼节孝悌,但凡自己的妻女在家里有些事情,也不论为何,从来都是要自家人谦让,久而久之,家里也都知道三房人的便宜好占。
老太太听不懂三儿子那些之乎者也掉书袋,对他礼重却不亲近。阮老太爷倒是得意这个有功名的儿子,却不插手内宅的事务。
阮青钰和母亲、妹妹在阮家的日子从来都算不得顺心。
此刻阮青钰把浸着鲜血的手举到阮老太太眼巴前了,老太太也不能当做没看见,问大姑娘阮青琅:“你既在场,说说是怎么回事儿吧。”
大姑娘细步上前,规矩得行了礼,“回祖母的话,青琅昨晚温书得晚了,早上一时起不来,去学堂没有这么早,青琅到时,四妹妹的手已经伤了。”
大姑娘阮青琅出现在学堂里时,一切确实已经发生过了。但她到得却没有那么晚,她到了门口,听到屋里有争执,三姑娘正哭诉说不过是她娘曾为舞姬,四妹妹就拿话讥讽她。
她料到有一场风波,便谁也没惊动,悄悄折了回去,在无人处坐了一会儿才又去学堂。
阮家大姑娘素来是最稳重的一个,事不关己不开口,阮青钰觉得也无可厚非。已经活过的那一世,阮家被抄时,所有嫁出去的姑娘都受了挂累,大姑娘阮青琅却还能在白知州的府上站住脚,手段可见一斑。
此时三少爷也出来说话:“祖母,四妹妹不仅欺辱我娘和妹妹,还信口攀诬我,我何时拿书刀吓唬过她。”三少爷阮塘和三姑娘都是周姨娘亲生的。
“三哥哥自然不会承认。我说你有,你说没有,可我手上的伤却是实实在在的。”他的确没有拿过书刀,但是他推了阮青钰。阮青钰知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谁也拿不出证据,只看断案的人,心在哪里。
三姑娘不甘,“大姐姐没看到,二姐姐可是看到了的。”
阮老太太看向二姑娘,她是大房赵姨娘的女儿。“我……我当时也是刚刚到,离得还有些距离,其中细节也不清楚,只是听到了四妹妹说什么跳舞啊的。”
和记忆中的一样,二姑娘不会站在自己这边。不像三姑娘明着和自己过不去,二姑娘似是和自己没有嫌隙,有时甚至显得很敦厚,却每每于关键处和她较劲。
阮青钰不知道何时得罪过二姑娘。事实上,很多事情,她直觉有不妥,却不明白为何。钱先生曾评价她,慧而善学,璞直未开心窍,于人情世故颇不通。家里人也有背地里称她“憨儿”。
阮老太太心中已然明了,如果事情真像三姑娘说的那样,那二姑娘不会含糊其辞,只会坐实是阮青钰的错。但今日之事,必要有惩罚,才可减绝家中争执。
“你们读了这么些书,女子当娴静,这点道理都不懂,也算是白读了。今日所有在场的,除了青琅,都回去抄三遍《女戒》。塘儿也不当参与姐妹口角,你是个儿郎,好好读书上进才是你该做的。罚你抄一遍《论语》。至于青钰,再去跪三个时辰祠堂。”
凭什么?
阮青钰差点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