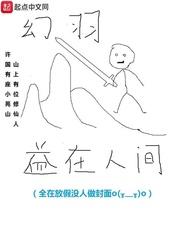笔趣阁>谁把龙袍披朕身上了(基建) > 7080(第21页)
7080(第21页)
晏生光意识清醒,坐起身来,无奈道:“阿娘,你想什么呢,安平县主手下能人众多,怎屑于虐待我。”
虽然她阿娘没有明说,但是她一定在脑子脑补了很多。
林苍:“你说你活下来了。”
晏生光:“安平县主并未虐待于我,还在回程之时为我准备的食物和水,我怕的是我转述的那些话让太子震怒。”
林苍不哭了,晏瑜的眉头也不皱了。
晏生光后怕地缩了缩身子,“阿父,安平县主不是一般人,大宸恐要变天。”
晏瑜脸色一变,“此话断不可在外说,如今文官武官皆要求出兵,那位安平县主威风不了几时了。”
晏生光摇头,“打不过的,他们打不过的,他们都未亲眼瞧见那惊雷的威力,太可怕了!”
晏瑜于林苍见晏生光的情绪又不对,急忙安抚起来。
晏瑜问,“你可曾见到黎县县令梁年?不知他有没有在安平县主手中活下来。”
晏瑜记得梁年,当年梁年不知为何差了一点没进殿试,晏瑜十分惋惜。
梁年为人清正,又不愿与京中之人交际,最后落了个黎县县令的官职。
若是这样好的人才,死在安平县主手上,那太可惜。
晏瑜觉得,以梁年的性格,想来是不会与安平县主同流合污的。
晏生光:“我直接见到了安平县主,未曾见过黎县县令,想来就算是见了,我也不知道。”
晏生光却深呼吸几口气,似乎是下定决心一般抬起头,他的牙齿在瑟瑟发抖,“阿父,安平县主治下宛如桃花源,也并未对我有什么为难,我们不能与安平县主作对,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有人弹劾她,知道有人让她去和亲,我还未去熙河路之时,她便什么都知道了。”
晏生光这几天终是想明白了,她甚至都在安京有探子,自己就当时卖她个人情,在殿上将这一事模糊着过去了。
这位在安京的探子想来也会安然无恙。
晏瑜的脸色立刻变了,“怎么可能,安京距离熙河路的路途这么远,你已是最快的速度,她怎么会比你还先知道?”
晏生光将脸埋进掌心里,“这便是安平县主的可怕之处,阿父,为了晏家,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在晏生光昏迷的这段时间,大宸的文官与武官一起放下曾经的针锋相对,明嘲暗讽,尔虞我诈。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都是林肆的错。
身为宗室女抗旨和亲,这是一错。
身为皇妹,辱骂太子,这是二错。
杀害朝廷命官,私造武器,意图谋反,这是三错。
都不用说上别的,光这三错,足以致命。
文官与武官达成合作,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但另一个近乎致命的消息传到了朝堂上。
瘟疫开始蔓延了。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也给正在兴头上的文官和武官浇了冷水。
若是此时打仗,跋山涉水,士兵全染上了瘟疫,岂不是得不偿失。
毕竟逆贼可不止林肆一个。
太子似乎也从愤怒之中抽离了出来,做了作为冷静的判断。
按兵不动,不管是林肆还是别的反贼,此刻断不能派兵出去。
*
林肆当然知道朝廷不会轻举妄动。
瘟疫会在接下来蔓延,除非太子真的是个弱智,执意要出兵。
熙河路早就做好了完全的预防准备,报纸上也提醒了百姓,整个熙河路的医者们也结束了培训,回到原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