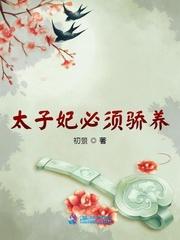笔趣阁>未来之雪域世界 > 7第 7 章(第1页)
7第 7 章(第1页)
发烧
陶佳与三十个土著雪民们组成长长的队伍,启程赶往海岸的第一天,天公作美,难得没起风雪。
大雪屋的废址被远远丢在后头,渐渐的再也看不见了。
只是午后时分,从高空中直射下来的阳光变得越发刺目强烈。
光线经过雪原大地上无数积雪冰晶的反射,几乎是无孔不入地散射进人的眼睛。
陶佳坐在被几个男雪民人力拉着往前的简易钢制雪橇上,小脸上正戴着她最大的一副墨镜,也还是有些觉得吃不消。
她的墨镜只是普通的大牌遮阳镜,并非全包围防护的护目镜或雪地镜。
虽然能隔离大量的紫外线,减轻刺眼程度,但两旁镜架处是镂空的,避不可免总有阳光会刺射进她的眼尾。
所以陶佳必须得时不时调整戴在头上的宽毡帽,以及从空间里拿出来包住她两侧头脸的一条羊绒围巾,才能尽可能地遮蔽住强光。
反观周围的那些雪民们,一个个戴什么样式防光用具的都有,在雪地里行进起来更是健步如飞。
他们在雪域里生活多年,早已习以为常。
像阿蒙和阿珍阿珠戴着的,就是陶佳在现代见过的那种球面雪镜。
又宽又大,遮住了她们的大半张脸,能有效地防光防风。
只是可能用的年数有些长,使用频率又太高,她们的雪镜上均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各种斑驳与划痕。
因此并不崭新,显得稍许陈旧。
男雪民里也有几个年长的,同样戴着那种雪镜。
然而他们所戴的明显损坏残缺,比如镜片破裂、镜架老化断裂、镀膜层严重刮花等。
一看就是阿蒙她们淘汰下来后,随手转赠给她们所爱重且排序靠前的丈夫们用的。
至于其他人,没有正经的雪地镜可以戴,就只能自己拣合适的兽骨,磨出两条并排的细缝,然后绑上绳子或皮筋,再戴在脸上。
那就跟过去因纽特人发明的雪镜一模一样了。
材料也很简单,随处可得,分外方便。
所有雪民里,只有阿花,陶佳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阿蒙她们那种雪镜。
不过大概率应该是没有的,不然就算她不戴,起码也可以暂借给她的其中一个丈夫戴。
阿花所乘坐的雪橇就在陶佳的雪橇后头。
同样被她的一个丈夫和其他两个公公爷爷辈的男雪民拉着,另一个丈夫则跟随在她的身边。
可能是为了挡阳光,她用红巾布蒙住脸的同时,又用一块厚实的皮料兜住头,揣着藏在衣服里的小婴儿,往后倚躺着十分放松,似乎已经陷入了梦乡。
俨然一副万事不管,呼呼大睡的样子。
陶佳没敢像她这样心大。
这片雪域对于她来说又大又空旷,前往冰川海边的路程又过于漫长陌生。
她的精神紧绷,始终没有办法轻易松懈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