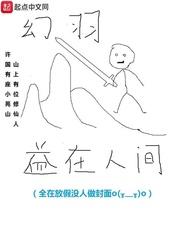笔趣阁>柯南:开局截胡明美,卧底酒厂 > 第213章 两个倔强的女人2更(第4页)
第213章 两个倔强的女人2更(第4页)
这样吧——补偿你两个最新款的芙绘莎包包怎么样?隨便你挑!”
宫野志保听到这个报酬,脸上的冰霜似乎融化了一点点,她瞥了一眼沙发上的贝尔摩德,又看了看森山实里,这才微微頷首:“行,成交。”
说完,她便不再理会森山实里,径直走到沙发前。
她將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几处狰狞的枪伤上,看著森山实里的初步处理,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语气带著专业性的严厉:
“你这处理得太粗糙了——消毒根本不彻底!甚至连无菌手套都不戴!是想让她感染而死吗?”
森实里无奈地摊手:“所以我说我不专业啊,不然也不会急燎地把你请来了。”
宫野志保不再废话,利落地打开医疗箱,找出无菌手套戴上,动作专业而迅速。
她看到贝尔摩德唇间还叼著的烟,毫不客气地伸手將其取下,直接摁灭在菸灰缸里,然后对森山实里吩咐道:“准备麻醉剂。”
贝尔摩德刻皱眉,强撑著表示:“我不需要那东西!”
宫野志保冷冽的目光扫过贝尔摩德倔强的脸,然后又看向森山实里,语气不容置疑,只有一个字:“打。”
森山实里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这两位姑奶奶,他听谁的似乎都会惹麻烦。
他只好硬著头皮打圆场,对宫野志保解释道:“贝尔摩德对很多种类的麻醉剂都过敏,不能用”
这倒不完全是假话,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確实可能对某些药物產生异常反应。
宫野志保闻言,盯著森山实里看了两秒,又瞥了一眼贝尔摩德,似乎判断出他没有说谎,便不再坚持。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按住她,別让她乱动。”然后便专注於准备手术器械。
贝尔摩德则对森实里说道:“再给我点根烟。”
森山实里心里嘆了口气,觉得这两个女人在某些方面真是像得可怕一样的倔强,一样的骄傲,一样的不肯在对方面前示弱。
他无奈,只好又给她点了一支烟,然后按照宫野志保的指示,在旁边负责递器械、拿药物,充当起临时助手。
宫野志保不愧是组织顶尖的科学家,不仅拥有极其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显然也有著出乎意料丰富的实战手术经验。
她的动作冷静、精准、高效,每一刀都恰到好处。
当她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將一颗变形的弹头从贝尔摩德的肌肉组织中取出时,涌出的鲜血立刻被她用准备好的止血材料和压迫手法冷静地控制住,整个过程没有丝毫慌乱,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普通的实验。
整个取弹过程持续了將近四十分钟,气氛压抑而紧张。
当最后一颗子弹被取出,所有伤口都成功完成止血和初步缝合后,宫野志保才微微鬆了一口气,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她脱下手套,看也没看一声不吭、只是默默抽著烟强忍疼痛的贝尔摩德,只是对森山实里交代道:“行了,让她好好休息。六个小时內不要喝水吃东西,注意观察有没有发烧感染跡象。“
说完,她便毫不留恋地转身,乾净利落地离开了房间,没有一句多余的问候或寒暄,仿佛只是完成了一项付费的技术服务。
森山实里一边开始收拾满是血污的现场,一边对虚脱在沙发上的贝尔摩德心有余悸地说道:“还好我当机立断把志保请来了—要是真让我自己硬著头皮上,胡乱取子弹,恐怕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贝尔摩德从鼻子里发出两声意味不明的轻哼,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儘管她对宫野志保怀著深刻的仇恨,但也不得不佩服对方那冷静到近乎冷酷的专业技术。
刚才那种情况,如果真让森山实里这个半吊子来处理,自己此刻恐怕已经因为大失血或严重感染而凶多吉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