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第二十九年春末 > 第 87 章(第1页)
第 87 章(第1页)
嘱咐几句便告辞了。
媳妇给一老一少都备好保暖的衣服围巾,一行人出了门。
一路上贾大爷牵着他的小孙女,步伐稳健,倒把个申无庸走得气喘吁吁,一路自嘲:“我在公园里练的都是些假把式,瞧贾大爷这身板,才是成天上山爬坡练出来的。”
同样体力不支的还有董迎春。她本来就是个宅家子,平常刷牙的时候做几个深蹲、偶尔跟着健身博主跳个操已自我感动的不行了。
在这冰天冻地的山坳里,风急风劲,她不单是腿走不动,呼吸也上不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竖着耳朵听大爷讲村里的事。
“我们村的人守的是宋墓,但整村迁到这里也就500多年的事……”
宝化村的故事有个传颂最多的版本——
这座宋墓建好后没多久,宋金开战,祖先被迫迁移到南方,其他村民散落各地,这里便荒废了。后人在南方历经朝代更迭,直到明代又有人当了大官,循家谱记录回来寻祖,发现祖墓早被淹于荒山。
起初该人只是时不时派人清理山土河泥、枯树败草,后来干脆在休官退隐后带着一家老小回来,重新建了宝化村。此后家族人丁不断壮大,又有不少外姓人来村里安家,到现在已是千人村落。
“其实不算是大墓,先人应该就是当地的父母官,不是啥皇亲国戚。专家说,咱平沃这样的墓原来可不少呢,二百座是有的,说明咱这地方好啊,风水宝地。就是可惜了,这一代一代下来,天灾人祸盗贼都太多,保存好的不多了。”
贾大爷一路都在为众人讲解,小孙女在旁边蹦蹦跳跳地走,时而咯咯地笑闹,一老一小看着丝毫不累,像四周的氧气都在这对祖孙鼻前似的。
唐子末常年在外面跑动,自然也不在话下,可与大爷比起来还是有差距。她说:“看到您老人家,就知道为什么宝化村世世代代能守住祖墓了。”
贾大爷受了这份夸奖,但也是个明白人,谦虚道,“姑娘只说对一半,我们只是普通百姓,再虎气那也只是力气大,脾气彪,也有力不足的时候,也得靠政策的帮衬。”
大爷望向远方,像望到过去一样的,“往以前说,明朝那位刚回来的时候,势单力薄,是靠着他的同僚帮忙,立了法令才保住这墓的;往近了说,政府要是不给我们那个牌子,我们光凭力气哪能成?以前专家刚来的时候,可全都是盗眼呐!”
他说的牌子,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是。”
“我们也是效仿古人。西汉王朝刚建立的时候,汉高祖为了稳定社会休养生息,专门派了20户人家住在秦始皇陵附近守陵。那20户人家和我们一样,你说是不是?也都是老百姓守墓嘛哈哈哈!”
董迎春喘着粗气,可还不忘由衷地赞他,“大爷你知识真丰富。”
“这话我给人讲了几十年啦,这村里谁都是导游哈哈哈哈!”
贾大爷调皮地开了个玩笑,并说,宝化村常有人过来参观,村里的人各个都能说出些历史典故来,对祖宗迁村守墓的故事更如数家珍,不奇怪。
唐子末也说,“是啊。隋炀帝也做过这样的事,为守先王帝陵,免除了附近十户人家的杂役,让他们专守。说起来,千百年来很多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
“我们村的人都可得意了!”贾大爷说,“觉得祖先了不起,也觉得自己了不起。喂,前边,快到了……”
其实山路修得很好,是平坦的柏油马路,只因为是上坡,大家才走得累哈哈的。
十几年前这条路刚修好后还有大卡车来往,把路轧得坑坑洼洼,村民们齐心协力向政府反映,硬逼得另开了一条路,让大车都绕行去了。
申无庸说,“在宝化村,你能处处感受到这个村子里的人是多么爱自己的家。人们成天喊‘要文化自信’,这就是吧?”
小孙女嗓子银铃似地,“我们村可好玩了!”
第40章宝化村旧事2
还很舒心和清闲。
唐子末看着祖孙俩,在羡慕他们的满足。这里的人似乎都这样,时间是别人的金钱,金钱也是别人的金钱,就连抬头仰望天空,都觉得这片天比别的地方更晴朗舒适些。
到了山上路势渐平,董迎春气也喘匀了,她随着唐子末的视线望向路一侧的陡壁,想象着春天这里该是什么样子。
北方的山是淡黄色的,像刀斧劈成一样的笔直,山腰树木稀疏,山顶又有茂密的枯树,山坳里湿气重时偶有薄雾缭绕,气质刚韧又不失温柔。
迎春低声自言自语,“我以前干吗不写这些……”
宝化村的故事唐子末和申无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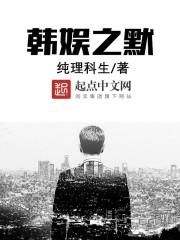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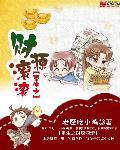
![和死对头甜甜恋爱[快穿]](/img/287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