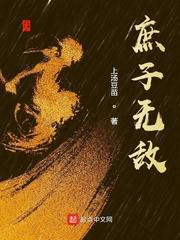笔趣阁>红楼琏二爷 > 第975章 敬茶(第2页)
第975章 敬茶(第2页)
宁桓准奏,并亲笔题写“文脉如国脉,不容断裂”八字,勒石立碑于国子监门前。
五月端阳,全国首次“女子学业统考”举行。一百七十所女校同步开考,科目涵盖语文、算术、法律常识与公共事务。试题由贾琏亲自拟定,其中一道论述题引发热议:
>“有人说:女子读书无用,终究要嫁人生子。请结合现实案例,论述此观点错在何处。”
扬州一名十四岁考生答卷流传天下:
>“我母原为佃农之妻,每日劳作十二时辰,不得休息。去年入女校旁听,学会记账与合同法,发现地主多年虚报亩产、多收租谷。她联合十余户村民提起诉讼,最终胜诉,退还粮款三百石。今我家已购田五亩,弟妹皆可入学。若母不识字,我们至今仍在饿肚。故曰:女子读书,不仅为自己,更为全家挣出生路。此岂谓‘无用’?”
此文被宁桓赞为“一字千金”,收入《新政典范文集》。
六月酷暑,贾琏主持“全国女教师大会”于明心讲舍。三百余名来自边疆、乡村、城市的女教员齐聚一堂,分享教学经验。会上,林婉儿登台演讲:
>“三个月前,我在草原一个小村授课。第一天,只有两个女孩敢走进教室。我说:‘你们有权来这里。’她们问:‘真的吗?’我说:‘真的,因为法律写了。’一个月后,全班十八人全部到齐。半年后,她们开始帮母亲写诉状、替姐妹争遗产。有一位学生告诉我:‘老师,我现在不怕黑夜了,因为我心里有光。’”
全场静默,继而泪流满面。
贾琏宣布:即日起,设立“星火奖学金”,每年遴选百名优秀贫寒女童,全额资助至大学毕业;同时推行“轮岗支教制”,所有师范毕业生须赴边远地区服务三年,方可取得正式教职。
七月十五,三年一度的科举预考拉开帷幕。令朝野震动的是,首批持女学结业证报名的二百三十七名女子通过资格审查,获得乡试资格。礼部官员仍试图阻挠,称“殿试无先例”,却被监察院当场弹劾“歧视性执法”。
宁桓乾纲独断:“既允其学,岂能拒其仕?明年会试,朕要亲自主持‘女子专场’,择优录用,授实职官位。”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亦举国振奋。无数小镇村庄响起鞭炮,家长抱着女儿奔走相告:“好好念书,将来也能做官!”
秋分时节,黛玉主持“皇家女子辩论赛”,议题为“女子是否应服兵役”。年仅十二的小公主力排众议:“男子可为国战死,女子为何不能守护家园?倘若敌人杀来,难道我们要等着别人来救?我要学射击、学急救、学指挥!”
贾琏得知,欣慰不已。他对黛玉说:“你看,种子已经发芽。我们播下的不是一本书、一所学堂,而是一种信念??她们开始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
冬至之夜,贾府设宴团圆。席间,平儿忽然提起:“二爷还记得当年您救下的那个卖身葬父的丫头翠儿吗?她如今已是苏州女校的数学教员,上个月还发表了论文《田亩计算中的误差修正法》,被农政司采纳推广。”
贾琏怔住,良久喃喃:“我还记得她当时哭着说:‘我不想一辈子被人买卖,我想知道为什么月亮不会掉下来。’”
众人沉默,唯有炉火噼啪作响。
次年开春,第一艘悬挂“女子航海培训班”旗帜的帆船驶离宁波港,十二名青年女学员踏上远洋实习之旅。她们将穿越东海,抵达琉球,学习国际法与海上救援技能。
而在西北戈壁,一座全新的“女子科技大学”破土动工。规划图上,图书馆居中矗立,四周环绕实验室、工坊与农田试验基地。奠基碑文由贾琏亲题:
>“此处不种金银,只栽希望;不筑高墙,专开大门。凡天下有志女子,皆可踏足此地,求真知,行大道。”
竣工典礼那天,贾琏携黛玉同至。春风拂面,黄沙渐绿。远处,一群少女正合力竖起旗杆,缓缓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蓝底金穗,中央绘着一本打开的书,书页化作展翅之鸟。
贾琏仰头望着,忽然觉得眼角湿润。
“你说,这条路还能走多远?”黛玉轻声问。
“只要还有人想读书,就永远不会到尽头。”他握紧她的手,“明远先生走了,但我们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火种,就在这些孩子的眼睛里。”
暮色四合,晚风送来远处学堂的诵读声:
>“我生来非为取悦他人,
>我学识只为照亮黑暗。
>法律赋予我权利,
>我以行动证明价值。”
贾琏闭目倾听,仿佛看见百年之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女孩都能昂首走在阳光下,不必低头,不必畏惧,不必沉默。
那一刻,他知道??变革已然发生。
而他们,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