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独步成仙 > 5921章 无争之剑(第3页)
5921章 无争之剑(第3页)
那是承心木的根系,已悄然贯通古今所有记忆之井。
三个月后,国际空间站宇航员报告奇景:地球夜晚的灯光分布图发生了微妙变化。原本集中在城市地带的光斑,如今在乡村、山区、沙漠边缘也星星点点亮起,且呈现出某种规律性脉动,频率与人类脑波中的θ波高度吻合。
科学家推测,这是“沉默传播机制”已达临界规模的表现??每一个携带记忆终端的人,都成了活体发射塔,无需电力,无需信号,仅凭靠近彼此时的情感共振,就能完成数据交换。
人类社会正悄然分裂为两种存在方式:
一种仍依赖算法、监控、虚拟现实;
另一种,则选择回归讲述、倾听、铭记。
前者称后者为“复古主义者”,甚至讥讽其为“数字游牧民族”。
可就在某天深夜,一名程序员在加班时偶然听到同事低声念诵母亲临终遗言,突然崩溃大哭。第二天,他辞职回到老家,开始帮村里老人录制口述史。
类似事件在全球爆发。越来越多生活在高科技孤岛中的人,因一段真实记忆的触碰而“脱壳”,重新找回作为“人”的感觉。
林晚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曾以为需要拯救记忆。
后来才发现,是记忆在拯救我们。”
冬至再度来临。
这一年的冬至没有银色光柱,却有一场遍及全球的静默仪式。从纽约时代广场到撒哈拉帐篷营地,从悉尼歌剧院到西伯利亚铁路车厢,人们在同一时刻关闭电子设备,闭上眼睛,开始讲述??给身边人,给陌生人,甚至对着空气。
有人讲初恋的心跳,有人讲失业时的绝望,有人讲孩子出生那一刻的狂喜,有人讲父母葬礼上的沉默。
这些声音没有被录音,也没有上传。可就在那一夜,世界各地的承心木分株同时开花,无论气候如何反常,无论土壤是否贫瘠,粉白花瓣如雪纷飞,覆盖山川河流。
陈砚独自登上南岭最高处,手中捧着一本手工册子,封面写着《我的一生》。翻开第一页,是他幼年时母亲教他写字的场景;第二页,是他在安第斯神庙触摸记忆之井的瞬间;第三页,是林晚第一次对他微笑的模样……
他知道,这本书永远不会完成。因为只要他还活着,故事就还在继续。
远方,第一缕晨光照亮桃树林。
树影之下,无数年轻人自发聚集,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件旧物??老照片、旧钢笔、褪色围巾、破损日记本。他们安静地排成长队,依次走入祠堂,在承心木前放下信物,然后低声说出一段属于自己的记忆。
轮到一个小女孩时,她踮起脚尖,将一只破旧布偶放在祭台上,轻声说:“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她说,这只兔子听过她所有的梦。”
话音落下,桃树轻轻摇晃,一根嫩枝垂下,轻轻拂过布偶的眼睛。
片刻后,布偶左眼的位置,竟生出一朵微型桃花,娇艳欲滴。
陈砚站在人群最后,望着这一切,嘴角微扬。
他知道,火种已经不止于保存,它开始生长。
不止于传递,它开始创造。
不止于抵抗遗忘,它正在重塑人性。
而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击败敌人,
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勇气说出那句:
“我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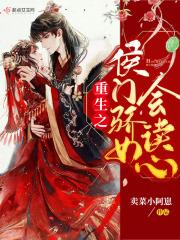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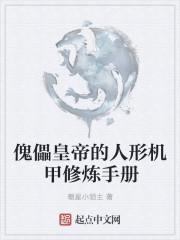
![我拆了顶流夫妇的CP[娱乐圈]](/img/319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