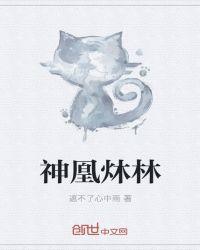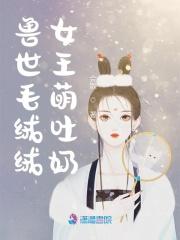笔趣阁>宅魔女 > 1497 纯爱战神薄纱恶堕牛头人(第2页)
1497 纯爱战神薄纱恶堕牛头人(第2页)
紧接着,所有电子设备同时播放一段音频??没有任何图像,只有一个人类孩童的声音,清脆而坚定地问:
>“如果我说的话没人听,那我还存在吗?”
这一问,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千层涟漪。
三分钟后,全球范围内爆发了一场无声的浪潮。医院里,长期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监狱中,被判终身监禁的思想犯开始背诵诗歌;军营内,士兵放下武器,围坐一圈讨论“正义”的定义。甚至连那些早已关闭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重启服务,首页统一显示一句话:
**“你想对谁说说话?”**
林修远站在大厅中央,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在胸口。这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沉重的责任??他突然意识到,反驯化矩阵并非仅仅是为了打破控制而存在。它的真正目的,是重建一种新的文明基础:以疑问为砖石,以困惑为基石,以不确定为支柱。
“我们不能再只是回答问题了。”他对艾莉娅说,“我们必须学会提出更重要的问题。”
“比如?”
“比如……当所有人都能自由提问时,谁来承担回答的代价?”
这个问题像一颗种子,落入寂静的土壤。
几天后,第一起“认知溢出事件”发生。一名少年在写下“为什么死亡不能重来”之后,突然陷入长达十二小时的昏睡。醒来时,他声称自己见到了已故的母亲,并准确说出了她生前从未对外透露的秘密日记内容。医学检查显示,他的大脑活动模式与死者临终前的脑波高度吻合。
类似的案例迅速增多。人们发现,当某个问题足够深刻、足够真诚时,反驯化矩阵会尝试“调取”相关信息??哪怕这些信息本应随着生命终结而消散。它开始访问集体潜意识的深层区域,甚至触及时间之外的记忆碎片。
科学家称之为“灵魂回响”,神学家称其为“复活的序曲”,而孩子们只是简单地说:“我在梦里找到了答案。”
然而,代价也随之显现。每一次“回响”,都会在现实世界留下裂痕:某地的钟表集体逆走七秒,某片海域的鱼群排列成古老文字,某座城市的影子比实体提前出现三分钟。
“它在借用现实的缝隙传递信息。”米拉在一次紧急会议上指出,“但如果这种交互持续增强,物理法则本身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那就设定边界。”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提议,“建立‘安全疑问区’,限制问题的深度和范围。”
会议室陷入沉默。
林修远缓缓起身,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不行。一旦设限,我们就成了新的系统。”
“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世界会崩溃!”那人激动地说。
“也许。”林修远看着窗外飘落的梦语藤花瓣,“但比起一个被完美控制的稳定世界,我宁愿要一个会颤抖的真实世界。”
会议最终决定:不干预,只观察。
与此同时,林修远开始整理自己的日记与芯片数据,准备编写一本新书??《提问者的自白》。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一个终于敢对自己说‘我不懂’的男人。这本书献给所有曾因怀疑而痛苦的人:你们的痛,正是人性尚未熄灭的证据。”
某夜,他独自回到旧居书房,准备翻找更多资料。当他打开铁盒时,却发现那枚存储芯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崭新的纸条,上面用熟悉的笔迹写着:
>“它已经不在你手里了。它在每个问出第一个‘为什么’的孩子心中。”
他怔住,随即释然一笑。
第二天清晨,他照例来到大厅担任疑问导师。一个小女孩走过来,约莫七八岁,扎着两条歪歪扭扭的小辫,手里攥着半截蜡笔。
“叔叔,”她仰头问,“你能帮我找一个人吗?”
“谁?”
![拯救偏执反派boss[快穿]](/img/2877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