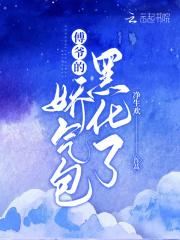笔趣阁>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堂中振奋人心激荡(第2页)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堂中振奋人心激荡(第2页)
那人未着朝服,却神态悠然,未近室,先朗声而入:“侄儿夜读,不觉困顿?”
朱标闻声,眼中浮现笑意,起身迎出几步:“皇叔怎会在此时至?”
朱瀚负手而入,笑道:“听说青策堂初开,你心念甚深,便过来看看。”
朱标目光落在案上策卷,低声道:“皇叔荐林复入堂,我已设为首座。他言辞锋利,却从不带半分私意。正是我所需之人。”
朱瀚点头,却不答。
他随手拈起几页竹简翻阅,眼神落在那几句“民欲政从”之语上,缓声道:“林复的策,讲的是人心,是理政之术。但这天下,不是只凭理便能治。”
朱标一愣:“皇叔是说。。。。。。”
朱瀚收起那卷策简,放回案上,语气温和却意味深长:“我只提醒你,策可解一时难,权却定百年局。你要借策为桥,渡的是人,不只是百姓,还有朝堂中的那群人。”
朱标垂首若有所思。半晌,他抬头看向朱瀚:“皇叔,我若愿以策取势,是否就能避开兵戈铁血,让这大明百姓不再受苦?”
朱瀚望着他,眼神中浮出一丝复杂:“避得一时,避不得一世。你能行策救世,是你的仁;可你要成就一番太平,终究还需有人,替你守得万一。”
朱标深吸一口气,郑重点头:“那侄儿就以策渡人,以义扶国,以德立世。”
朱瀚微微一笑:“如此,便好。”
三日后,青策堂设于东宫偏院之内,门额由太子亲书“青策堂”三字。
堂中无金玉装饰,无丝竹鼓乐,仅置长几数列,文案简洁,墙上挂着时事图卷与舆图。
初堂之日,除林复为首座,尚有八人应召,其中有游士、寒儒、郡吏、小贩、医者,皆非朝中旧臣,却各具一技之长。林复亲自引众入堂。
“此堂不同朝议,不拘礼仪,只讲真言,不避高下。”
林复一语落下,众人便知青策堂非空名之设。
堂中静默片刻,一位身形瘦削,衣着朴素的青年抱拳道:“草民王潜,原是南郊市井贩药之人,前些日子亲历中疫疾。医方不通、诊治迟缓,致百余人罹患,草民不才,愿献策疏其因。
林复微一点头:“细说。”
王潜顿了一下,道:“其一,因郡县所设仓医,多由人事推选,非医而医;其二,诊所与医馆皆设城中富坊,郊民行数十里而不得治;其三,药材缺乏,不是无钱,是无人引。”
堂中诸人纷纷点头。一名年长者叹道:“此言极是。老夫家乡遇过酷寒,三月之病,五月方医,民何以安?”
林复看向朱标,眼神微挑。
朱标颔首:“王潜之言,可书之。再议。”
接下来的三日,青策堂接连上议,所涉皆非朝政大策,而是庶务细节。
有议官仓粮收法,有论新法后衙门冗役之重,有陈工坊织女之疾,也有倡书塾学制之弊。
堂中日益热络,太子频频出入听议,甚至偶作笔记,与众人探讨。
而在一日议毕后,林复独坐廊下,望着庭中新栽的青松出神。
忽听身后脚步轻响,他不回头,道:“王爷竟至此地,倒是稀客。”
朱瀚缓步入廊,笑道:“你我之间,何须虚礼。”
林复一笑:“王爷观今日议事,有何感想?”
朱瀚却不答,只反问道:“你知‘策’为何物?”
“愿闻其详。”
朱瀚坐于石凳之上,缓缓说道:“策者,智也。智者可胜愚,可敌强。可你若将策拘于书简,拘于口辩,不过纸上画饼。
林复眉头轻动:“王爷之意,是我空谈?”
“非也。”朱瀚轻叹,“你的策有实心、有真意,却无血肉。你讲百姓冷暖,却不知那冷暖之后,真正能动其命者,是人,是势,是你们现在未曾接触的一群人。”
林复沉默片刻,忽道:“若王爷有更深之谋,不妨直言。”
朱瀚看他一眼,语气忽然低沉:“我等一事,三年矣。而今太子设堂,士心可用。你若愿,便与我共下一盘真棋。”
林复转身,眼中神色难辨:“若此棋落错?”
“落错也无悔。”朱瀚笑意浅浅,“因这盘棋,不只为太子,更为天下。”
数日后,京中传闻青策堂之议有成,太子亲裁百案,皆为民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