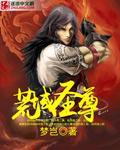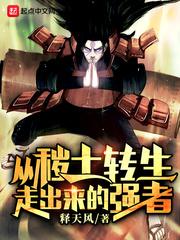笔趣阁>那年花开1981 > 第五百三十八章 装大款是门大学问(第2页)
第五百三十八章 装大款是门大学问(第2页)
他看完,只说了一句:“把上次整理的账目,连同所有合同副本,一起寄给市纪委、经委、国资委,三份,挂号。”
马兆先吓了一跳:“你疯了?这可是正式举报!”
“不是我举报,是组织监督。”李野淡淡道,“他们要开会,我就让他们开个够。他们要整人,我就让上面看看,谁在整谁。”
三天后,市经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进驻西南重汽。调查重点正是资金流向与管理模式冲突问题。与此同时,一分厂生产的首批新型卡车在展销会上大获成功,订单暴增,媒体争相报道,标题赫然是《改革先锋:一分厂模式能否复制?》
舆论压力之下,董善被迫暂停对陈志明的处理决定。但他并未罢休。
一周后,西南重汽传出消息:因“成本控制需要”,取消所有外派人员的交通补贴与住宿津贴。陈志明等人一夜之间住进了漏雨的旧工棚,每天通勤两小时。
李野得知后,立即下令:“从今往后,一分厂承担所有外派人员的生活费用,标准照旧。另外,每人每月加发五百元‘艰苦岗位津贴’。”
消息传开,西南厂内震动。许多原本观望的基层工人开始悄悄打听一分厂的管理制度,甚至有人主动找陈志明请教质量控制手册。
董善终于坐不住了。
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怒吼:“李野这是在收买人心!他想把西南变成他的一言堂!”
没人回应。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他知道,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会议上,而在每一天的生产线上,在每一道工序的执行中,在每一个工人的选择里。
一个月后,奇迹发生了。西南重汽第三车间首次实现连续七天零废品,月度考核首次达标。陈志明在总结会上放了一段视频:一线工人自发组织夜校,学习一分厂的操作规范,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我们要做精兵,不做废料”。
视频传回奉天,李野看着看着,眼眶有点发热。
柯老师站在他身边,轻声道:“你看,人心是肉长的。你给尊严,给希望,给路,他们就会跟着你走。”
李野点点头:“可这条路,注定有人要挡。”
果然,第二天,董善以“防止技术泄密”为由,禁止一分厂资料在西南厂区流通,并下令封锁陈志明办公室,查抄所有文件。
陈志明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交出钥匙,然后当着众人的面,背诵出整本《质量管理条例》和《安全生产规程》。
围观工人一片寂静。
当晚,超过两百名工人自发聚集在厂门口,举着自制的牌子:“我们要标准!”“我们要效率!”“还我陈科长!”
事态迅速升级。市里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责令西南重汽立即恢复陈志明职务,并保证外派人员合法权益。
董善被迫低头。
半个月后,李野亲赴西南重汽,在全厂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没有批评任何人,只是讲述了三分厂当年如何从濒临倒闭走到今天的全过程。他说:“我没有救世主的心态,我只有一个信念??工人不该被当成消耗品,企业不该靠关系活着,改革不该只为少数人谋利。”
台下掌声雷动。
会后,辛琦私下约见李野。两人坐在厂区后山的小亭子里,许久无言。
最后,辛琦开口:“你赢了。”
“我没想赢。”李野望着远处渐渐亮起的厂房灯光,“我只是不想输。”
辛琦苦笑:“你知道董善背后是谁吗?”
“猜得到,但不想点破。”李野淡淡道,“只要我还在这一体系里,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够了。但我有一条底线??不能动一分厂的根,不能寒了工人们的心。”
辛琦点点头:“我会压住董善。但你也得给我时间,让我把这艘破船慢慢调头。”
“我等得起。”李野说,“只要方向是对的。”
三个月后,西南重汽首次实现季度盈利。次品率下降至历史最低,工人收入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更令人震惊的是,已有三家外地车企主动联系一分厂,希望引入其管理模式。
马兆先乐得合不拢嘴:“咱们这是要开宗立派了!”
柯老师却依旧皱眉:“树大招风。现在盯着咱们的人,不只是董善了。”
李野站在新落成的研发大楼前,望着晨光中的厂徽,轻声道:“那就让他们看。只要我们走得正,行得稳,谁也扳不倒。”
风吹过厂区,带来远处装配线上传来的金属撞击声,清脆、有力,像心跳,像鼓点,像一场无声的进军。
他知道,这场改革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前方还有更多的山要翻,更多的关要闯。但他不怕。
因为他身后,站着十万相信“好好干活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工人,站着一群愿意跟他一起赌未来的兄弟,站着一个从未真正死去的信念??
**劳动,不该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