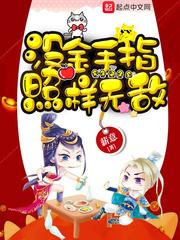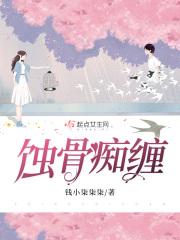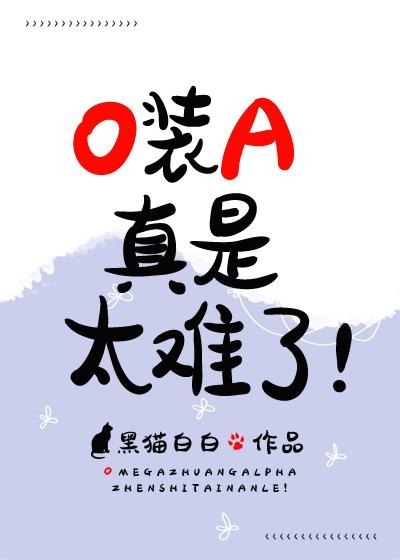笔趣阁>求求了,快回家练琴吧 > 564 璀璨给我解中(第2页)
564 璀璨给我解中(第2页)
一个小女孩举手:“姐姐,你小时候也被骂过吗?”
“骂得可狠了。”黄楚贤笑着点头,“有一次我把作业本上的五线谱写成了漫画,我妈气得让我抄十遍音阶表。”
孩子们哄堂大笑。
另一个男孩怯生生地问刘子谦:“你真的会爵士?能不能教我们打beatbox?”
刘子谦愣了一下,随即笑了:“beatbox我不太行,但我可以教你用钢琴模仿鼓点。”
他走到琴边,双手砸出一段funky节奏,左手低音跳跃,右手切分音凌厉干脆。孩子们瞪大眼睛,纷纷跑上前摸琴键。
卢瀚文蹲下身,问一个瘦小的男孩:“你喜欢唱歌吗?”
男孩摇头:“我不敢,同学说我跑调。”
“我小时候在超市唱歌,顾客都停下来听。”卢瀚文认真地说,“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我唱的时候,心里想着我喜欢的人能不能听见。”
男孩抬头看他,眼里有了光。
张禹舟拿出那盘母亲留下的录音笔,按下播放键。
沙哑却温柔的女声缓缓响起:
>“小星星,亮晶晶,挂在天上放光明……”
>
>“宝贝,这是妈妈给你写的歌,你要记得,不管你在哪,只要听到星星闪的声音,就是我在陪你。”
整个教室安静下来。有孩子偷偷擦眼泪,有老师背过身去擤鼻涕。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张禹舟轻声说,“哪怕只会唱一句,那也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临走时,校长握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放:“很多年了,没人来告诉我们,音乐不只是特长生的事。”
“现在有人来了。”李安说,“而且,我们会一直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辗转七座城市,走过十二所学校,举办了十五场非正式音乐会。每一场都没有聚光灯,没有直播镜头,却比任何一场商演都更让他们感到充实。
在一所聋哑儿童学校,他们尝试用手语配合旋律,让孩子们通过地板震动感受节奏。当马可用低频合成器模拟心跳声时,一个从未开口说话的小女孩,竟跟着节拍轻轻拍手,脸上绽放出灿烂笑容。
在山区小学,停电的夜晚,他们借着手电筒的光,在操场上弹琴唱歌。孩子们围坐在周围,仰头看星星,有人轻声说:“原来音乐和星星一样,是不会熄灭的。”
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某所戒网瘾矫正中心。那里收容了许多被家庭放弃的“问题少年”。负责人原本只允许他们做一次心理疏导性质的访问,没想到,当卢瀚文唱起那首《修车铺的夜》,一个始终低头沉默的少年突然抬起头,哽咽着说:“我爸……也是修车的。”
那天晚上,七个“听见者”留下来,陪他们聊到凌晨。有人讲父亲酗酒,有人说母亲改嫁后再也不愿认他,还有人坦白自己逃学打架,只是为了引起父母注意。
黄楚贤当场写下新歌片段:
>“我不是坏小孩,我只是迷路了
>家的方向太久没亮灯,我以为再也回不去了……”
她唱完,整个房间鸦雀无声。然后,一个接一个,少年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安后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原以为是去拯救别人,其实是他们在救我们。因为当我们看见他们眼中的光,才真正确认,我们的存在有意义。”
三个月后,“听见者”项目正式被教育部纳入“美育振兴计划”试点工程。政府拨款修建流动音乐教室,配备基础乐器,培训乡村教师。而他们的巡演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求求了快回家练琴吧#”话题累计阅读量突破百亿。
更令人意外的是,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行动。
一位退休交警组建了“银发摇滚团”,在公园排练披头士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