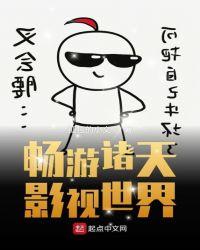笔趣阁>亮剑:我有一间小卖部 > 第一千四百一十三章(第1页)
第一千四百一十三章(第1页)
听完小丽莎的话,艾丽莎沉思了片刻后,从履行箱翻出了一只勃朗宁M1906。
枪和子弹是分开放的,艾丽莎找出子弹后,开始在为弹夹压上子弹。
小丽莎看着,叹了一口气,“艾丽莎,你最好别杀人了。”。。。
夜色如墨,潮声低回。小卖部门口那盏煤油灯在风中摇曳,光影在斑驳的墙上爬行,像无数未眠的灵魂正悄然低语。徐三没有进屋,而是坐在门槛上,手里摩挲着那枚子弹壳,壳身早已被掌心磨得发亮,边缘却仍带着战争留下的毛刺。他望着海面,远处黑沉沉的水波仿佛藏着无数双眼睛,静静注视着这片曾被炮火撕裂的土地。
突然,风铃又响了??不是被风吹动,而是被人从外轻轻拨动。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门口,披着破旧斗篷,脸上蒙着半幅黑纱,只露出一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是那位痴呆老太太,今早三位歌手之一。她没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放在门槛上,转身便走,脚步竟出奇地稳。
徐三拾起纸片,借灯一看,心头猛地一震。纸上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井底的小孩,会唱歌。”下面还画了一条波浪线,像是声波,又像一道裂缝贯穿大地。
他立刻起身冲进广播机房。艾丽莎正趴在示波器前,耳机戴了一半,眉头紧锁。
“你怎么来了?”她抬头,“我刚截获一段新信号,来自同一个坐标,但这次……不是敲击,是人声。”
“人声?海底?”
“嗯。极微弱,混在洋流噪声里,像是……哼唱。”她按下播放键。
音箱中传出一段断续的童音,唱的是《小白菜》,调子走得很远,每个音都像被海水拉长、扭曲,却又透出一种奇异的纯净。那声音不似活人所发,也不像录音残留,倒像是某种记忆的残影,在地质层中反复震荡后重新浮现。
“频率分析出来了。”艾丽莎指着屏幕,“和今天下午老歌手们的演唱高度共振。尤其是第三遍《茉莉花》时,海底回应的旋律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模仿’我们的节奏??就像……它在学习。”
徐三沉默良久,忽然问:“有没有可能,那不是‘他们’在唱歌,而是‘我们’唤醒了什么?”
“你是说……集体创伤形成的声学记忆?”
“不止是记忆。”他低声说,“是情感的化石。当特定频率响起,那些未曾安息的情绪就会被激活,通过水、金属、岩层传播。老陈说过一句话:‘有些死人不肯闭眼,是因为话还没说完。’”
艾丽莎摘下耳机,手指微微发抖。“所以《灯》系列不是纪录片,是钥匙?每集播出,都在打开一层封印?”
“也许从第一集开始,我们就已经触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徐三望向窗外,“但现在已经不能停了。”
次日清晨,吴港传来消息:第二批潜水员已准备就绪,携带新型耐压麦克风与共鸣增幅器,计划深入飞鱼号残骸内部。带队的是曾在太平洋战场打捞过三艘沉舰的老兵林海??七位深海幸存者中唯一始终沉默的那个“林”。
他在出发前找到徐三,第一次开口:“我要带一件东西下去。”
他从怀里掏出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上面刻着模糊的汉字:“昭和十七年?海军慰安所?编号09”。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他说,“她不是战俘,也不是妓女。她是自愿去的,为了换一张船票,让我能逃出南京。她在信里写:‘儿子,如果有一天你听见海里有女人唱歌,请替我说对不起。’”
徐三看着他,终于明白为何林在归航仪式上要抓一把沙塞进口袋??那是他从未踏足的故乡土壤。
“你可以录一段她的信吗?”徐三问。
林摇头:“我不敢听。怕一听,就再也游不动了。”
六点整,潜水队出发。海面平静得反常,连浪花都像是被按住了喉咙。徐三、艾丽莎、玛琳及几位核心成员守在监听站,耳机连接深海麦克风,屏息等待。
七点十二分,信号首次接通。
“已抵达残骸外围……天啊……”潜水员的声音颤抖,“舰体不像坍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撑开了。走廊还能通行,钢板上有划痕,不是腐蚀,是人为的……像是有人在里面生活过。”
接着,是一阵漫长的静默。
然后,另一个声音响起:“发现舱室……门上有字,用刀刻的……‘勿入’,下面还有小字:‘我们活着,但不想被救。’”
徐三浑身一震。
“继续前进。”林的声音突然插入频道,“我去。”
十分钟后,林独自进入主控室。画面因水流扰动变得模糊,但音频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