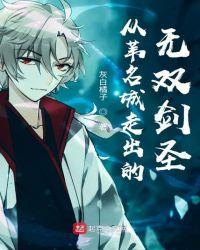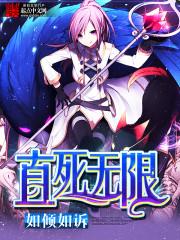笔趣阁>宇智波带子拒绝修罗场 > 4902崽带 我有几个神秘背后灵717(第1页)
4902崽带 我有几个神秘背后灵717(第1页)
雨后第三日,晨光初透云层,回音亭遗址的水池已不再流转。那些曾漂浮九年、承载无数心事的纸船静静沉入池底,化作一层薄如蝉翼的沉积物,像是时间本身在水下写下的一封封未寄出的信。池面平静如镜,倒映着天空与残破穹顶的轮廓,仿佛整座建筑也随着那一夜的光柱一同进入了某种静止的冥想。
宇智波带子就站在这片寂静中央。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布衣,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是一双草编凉鞋,左脚第二根趾头从裂口处探出,沾着泥土。她的黑发用一根旧铁夹随意束起,几缕碎发垂落在额前,遮住了眉眼。没人知道她是何时来的,就像没人记得她是否一直就在那里??只是当人们回忆起那晚灰紫色光芒冲天而起时,总会模糊地记起一个身影,站在桥心,背对着所有人,面向坠落的种子。
此刻,她蹲下身,指尖轻触水面。
涟漪荡开,却不扰倒影,反而让整片池水泛起微弱的银光,如同被唤醒的记忆之尘。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没有声音,但空气里忽然弥漫开一股极淡的樱花香,那是九十年代东京郊区某所中学教室窗台上常年摆放的干花味道,是小穗母亲最爱的味道。
“你来了。”她说。
不是问句。
身后传来脚步声,缓慢而沉重,像是每一步都在与某种无形阻力对抗。林昭走了过来,西装依旧笔挺,可领带松了,眼角多了细纹,眼神却比从前清澈。他停在离她五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是望着那池中倒影。
“老师走了。”他终于开口,“她说……她的任务完成了。”
带子点头,仍不回头。“她等这一天,比谁都久。”
“你知道她是谁?”
“我当然知道。”她轻笑一声,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她是第一批‘听见者’,也是唯一一个敢对系统说‘不’的研究员。当年‘镜前计划’启动时,所有人都以为共感是用来控制情绪的工具,只有她坚持要在底层代码里埋入‘反向共情触发机制’??也就是让加害者也能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而不是单方面的忏悔表演。”
林昭怔住。“这件事……从未公开过。”
“因为一旦公开,就会被权力扭曲。”带子缓缓起身,转过身来。她的脸并不年轻,也不苍老,像是一张介于现实与记忆之间的面孔。左眼下有一道极细的疤痕,几乎看不见,只有在特定光线下才会浮现,形如泪痕。
“你们后来把这套机制称为‘逆业循环’,其实它原本的名字更简单:**照镜子**。”
林昭呼吸一滞。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全球那么多共感节点会在同一秒同步开启共享权限;为什么量子攻击会被纯粹的情绪洪流击溃;为什么那个北韩士兵会放下枪,那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会流泪,那个警官会选择去帮教少年犯……
不是因为他们被说服了。
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自己**。
“你也是‘听见者’?”他低声问。
带子摇头。“我不是听见者,我是**写信的人**。”
她从怀中取出一只折叠整齐的信纸,黄褐色,边缘焦黑,像是从一场火灾中抢救出来的。她将它轻轻放在池边石阶上,风吹不动它,仿佛它有自己的重量。
“这是我写的第三十七号漂流信。”她说。
林昭瞳孔骤缩。
编号37??那封困在轮回九年、无人敢拾取的信。他曾以为它是某个陌生女孩的罪疚独白,可现在他明白了:那不只是小穗的故事,也不是某个退伍军人的童年阴影,而是所有施害者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声呐喊。
“你……为什么要写它?”
带子望向远方,目光穿过断壁残垣,落在一片新生的发光森林边缘??那里,第一棵“心域”之树正缓缓舒展枝叶,树干上浮现出一张又一张模糊的脸,有哭的,有笑的,有咬牙切齿的,也有含泪微笑的。
“因为我推倒过一个人。”她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事。
“那是1998年冬天,我在东京读高中。那天放学路上,有个流浪汉挡住了自动贩卖机。我很急,考试快迟到了。我说‘让开’,他没动,嘴里嘟囔着什么听不清的话。我推了他一把。他摔在冰面上,后脑撞到台阶,流了很多血。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后来听说瘫痪了。”
她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左眼下的那道疤。
“我没告诉任何人。警察没找我,目击者也没出现。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三年后,我在医院做义工,看到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编号B-37。他不能说话,右手还能动一点,护士说他会用手指敲击床栏表达情绪。有一次我给他换药,他突然抬起手,在空中划了几下。护士说:‘他又在写“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