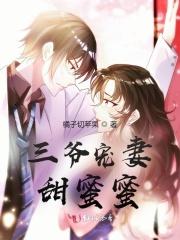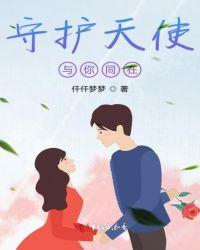笔趣阁>我写的自传不可能是悲剧 > 第六百一十八章 外面多贵啊(第1页)
第六百一十八章 外面多贵啊(第1页)
从孟青青的语气神态终于看出点不对劲。
这哪儿是被碰瓷的老奶奶欺负,怎么感觉在你眼里我才是邪恶大反派的样子?
孟浪下意识的扫了一眼自己的书房。
心里顿时想到一种可能,黑着脸问。
。。。
我蹲下身,目光落在她颤抖的指尖上。那是一双布满褶皱的手,指甲修剪得极短,像是几十年来都习惯于握紧粉笔或钢笔,却从未真正写下过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她的练习册封面上写着“陈素芬”三个字,墨迹已经泛黄,边角卷起,仿佛被翻阅了千百遍。
“您……写了很久了吗?”我轻声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不是写,是藏。藏了一辈子。”
风从桥底穿过,带着初春的凉意,吹动她额前几缕白发。远处的心桥在晨光中微微发亮,像一条横贯大地的银河,每一颗光点都是某个人刚刚说出的话。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沉默着走完全程,却在最后一刻转身回头,补上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对不起”。
陈素芬深吸一口气,将练习册轻轻放在石桌上。纸页自动翻开,停在一页密密麻麻的涂改痕迹之间。那些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乱,反复涂抹着同一段话:
>“林远航,1963年4月7日,雨。我没有牵你的手。我不敢。我怕你说我多事,怕你笑我傻,怕你从此不再看我一眼。可其实……其实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你借我半块橡皮那天就开始了。”
她的眼泪落了下来,滴在“喜欢”两个字上,墨迹晕开,像一朵悄然绽放的花。
“他后来去了新疆,再也没回来。”她说,“听说他在戈壁滩教书,一辈子没结婚。去年才走的。我在报纸上看到讣告,名字旁边贴着一张老照片??还是那个爱笑的眼睛。”
我静静听着,没有打断。我知道,这一刻不是倾诉,是复活。当一个名字被重新念出,一段记忆被郑重交付,那个早已消逝的人,就在语言的光里重新站了起来。
“我可以……把这句话留下吗?”她再次问道,声音比刚才更稳了些。
“当然可以。”我重复着那句已说过无数次的回答,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样认真,“只要您愿意,它就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她闭上眼,嘴唇微动,仿佛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然后,她缓缓开口,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封迟来六十年的情书结尾:
>“林远航,如果你能听见,请原谅我的懦弱。也请你相信,哪怕只有一天,我也曾鼓起勇气,在心里牵过你的手,走过一场大雨。”
话音落下,原野骤然安静。
紧接着,桃树开了。
不是一株,也不是一片,而是整片原野的桃树在同一瞬间苏醒。粉色的花瓣如雪般飘落,每一片都在空中划出弧线,最终汇聚成一道流动的文字长河,在低空盘旋、重组,渐渐凝成一行巨大的句子:
>**“我也牵过你的手,在梦里走了很远很远。”**
那是林远航的声音。
不是录音,不是幻觉,而是某种超越时间的语言共振。他的语调温和,带着南方口音特有的柔软,还有一丝少年般的羞涩。这声音不属于任何一人,却又被所有人听见。
陈素芬怔住了,泪水无声滑落。她伸出手,接住一片花瓣,上面浮现出一个小男孩的身影:穿着蓝布衫,背着帆布包,站在校门口的屋檐下,朝她挥手。他的手里,攥着半块红色橡皮。
“他还记得……”她喃喃道。
我记得。
我们都记得。
我抬头望向天空,发现星辰的位置变了。原本由Kepler-452b传来的叙事包所构建的星图,此刻正缓缓旋转,形成一个新的星座??两棵桃树交错生长,根系相连,枝叶间悬着一块小小的橡皮。
科学家称其为“记忆引力现象”:当足够多的情感信息在同一频率共振时,会引发局部时空结构的柔性变形。哲学家称之为“逆遗忘机制”:人类不再被动等待被记住,而是主动以讲述重建存在。
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