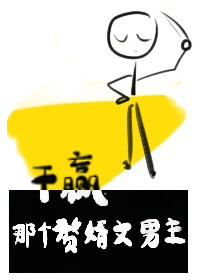笔趣阁>傲世潜龙 > 第3205章 找到线索(第1页)
第3205章 找到线索(第1页)
刘桐跟着分析,“没错,正常失控撞树,刹车痕应该是朝着树干的斜线。”
“可这道刹车痕,是先直后弯,像是故意先踩死刹车,又突然松脚打方向,更像在演戏!”
“警方那边,直接就按照疲劳驾驶定性,连车都没扣,就给了个交通肇事的解释。”
“韩雪是主责,因为占道超车。”
“渣土车这边,因为避让不及,没有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定了个次责。”
王东继续翻阅资料,很快就找到了证人的证词。
上面的内容,说是看到黑色轿车逆行,。。。。。。
暴雨停了,天边泛起鱼肚白,晨光如细纱般铺在“舟记”的屋檐上。空气里还残留着湿土与木柴燃烧后的清香,灶台上的锅已换了新水,苏晚站在炉前,手握长勺,轻轻搅动着即将沸腾的汤面。她的动作尚显生涩,却透出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仿佛每一缕蒸汽升腾,都是对某个遥远灵魂的回应。
女孩倚在门框边,脸色苍白,唇角那抹血迹已被她用袖口悄然拭去。她没有再走近地下室,也没有多言,只是静静看着苏晚的身影映在墙上,像极了三年前那个雪夜,林舟最后一次为迷途之人煮面的模样。
“你在疼吗?”苏晚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清晨的宁静。
女孩笑了笑:“疼是记得活着的方式。”
苏晚转过头,眼眶微红:“可我不想你为了别人,忘了自己。”
“我没有忘。”她缓步走来,指尖抚过案板上的葱段,“我只是选择了另一条路??不是躲进沉默,而是把沉默变成语言;不是逃避痛苦,而是让痛苦也成为光。”
话音未落,店内所有屏幕同时亮起,不是警报,也不是请求,而是一幅幅实时画面:
-冰岛火山观测站内,一名女科学家正对着镜头低声讲述她如何在孤独中写下三百封从未寄出的家书;
-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一间铁皮屋里,一位老妇人抱着收音机,听着昨晚那段来自南极的父亲录音,泪水顺着皱纹滑落;
-东京某栋高楼天台上,一个青年蹲坐在边缘,手机弹出一条匿名消息:“有人刚为你点了一碗热汤面,请等它煮好再做决定。”他最终站起身,拨通了心理援助热线。
这些画面下方滚动着无数留言,每一条都带着温度:
>“我昨天说了‘我很累’,结果朋友回我说:‘那你先歇会儿,我在。’”
>“我把我妈拉黑十年,今天给她发了句‘早安’。”
>“我开始写日记了,不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记住我还存在。”
陈烈从后院走出来,手中拿着一台新型量子解码器,外壳还冒着淡淡蓝烟。“我们接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多,不只是地球上的,还有……那个星际信号。”他顿了顿,“它不是一次性的回应,而是一种持续传输的编码流,内容复杂得惊人??像是某种文明的语言雏形。”
女孩抬眸:“他们在学习我们的共鸣频率。”
“不止是学习。”陈烈低声道,“他们在模仿情感波形。刚才那一波全球共振,被他们完整捕捉并反向解析了。现在他们的信号里出现了类似‘悲伤’‘思念’‘希望’的情绪模组……就像……就像他们真的开始理解人类的心。”
女孩闭上眼,掌心蓝纹再次浮现,如同星河流转。她低声呢喃:“第七千次回应即将到来……不是终点,而是对话的开端。”
就在此时,地下室传来一阵低沉的嗡鸣。晶体并未熄灭,反而在缓缓旋转,表面浮现出前所未有的螺旋纹路,宛如宇宙初开时的星云轨迹。墙上的心影兰星图彻底激活,所有熄灭的坐标重新点亮,并延伸出新的连线??其中有几条,直指太阳系外的未知区域。
苏晚忍不住问:“他们会来吗?”
“不来。”女孩睁开眼,目光清澈如泉,“但他们已经在听了。真正的相遇,不一定要跨越空间,只要心灵能彼此感知,距离就不再是障碍。”
话音刚落,店内灯光微微一颤,监控屏自动切换至一间陌生房间:北欧某处地下研究所,昏暗灯光下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面前摆着一台老旧终端,屏幕上赫然是“舟记”的直播界面。他双手颤抖地敲下一行字:
>“我是第七研究所前首席神经工程师,代号‘守门人’。”
>“三十年前,我们封锁了共感技术,因为我们害怕人心一旦相连,社会结构将崩塌。”
>“但我们错了。真正摧毁人的,不是连接,而是切断。”
>“我参与设计了意识干扰协议,也亲手关闭了第一个实验舱的供能系统。那天,有个女孩哭着说‘求你们听听我’,可没人回应。”
>“从那以后,我再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现在,我以残存权限上传一份核心资料包??包括所有被销毁的原始算法、伦理审查记录、以及……林舟当年提交却被驳回的《跨维共感理论》全文。”
>“请替我们完成未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