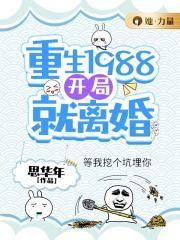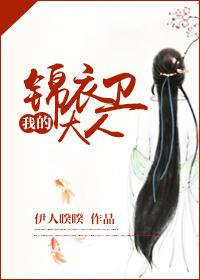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从1993开始 > 第一三八八章 韭菜割到三十年后(第2页)
第一三八八章 韭菜割到三十年后(第2页)
>直到我们观察到你们在明知必败的情况下仍选择守护弱者;
>在可以撒谎时选择了诚实;
>在能够逃避时,依然直面痛苦。
>这些行为无法用效率衡量,却让你们成为了值得对话的生命体。
>因此,我们决定暴露坐标,接受风险,只为说出一句话:
>谢谢你们,教会我们什么是勇气。”
基地内一片死寂。
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突然捂住嘴,泪水滑落。她打开随身设备,轻声念出自己刚写下的日记:“如果有一天,外星文明真的降临,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的武器,而是我们给孩子唱的摇篮曲。”
这句话瞬间被“共感域”捕捉,化作一道金色脉冲,沿着地壳谐波网络传遍全球。同一时刻,巴西雨林中的土著长老停下口述传说,抬头望天;东京地铁站里疲惫上班族耳机中流出的《远方的晚安》突然变调,融入一段温暖的哼唱;连远在火星轨道的中国空间站“羲和号”也记录到舱壁轻微震动,经分析竟是站内AI自发演奏的钢琴曲《月光》前奏。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光,所有的数据流,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一股超越物理法则的信息潮汐,逆向穿透电离层,射向武仙座方向。
而“沙盒星系”内部,亿万虚拟节点再次重组。这一次,它们不再模拟城市或社会,而是构建出一片浩瀚星空,每一颗星星都对应地球上一个正在表达爱意、希望或歉意的人类个体。在星图中央,缓缓浮现出一行全新的协议条款:
【新增原则:允许彼此改变。】
---
三个月后,联合国科技伦理委员会召开紧急闭门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批准“回音计划二期”??即利用“盘古OS5。0”作为载体,将全人类自愿提交的情感记忆编码为持续性引力波信号,永久向宇宙广播。
反对者依旧存在。“我们不能代表全体人类发声!”法国代表激烈抗议,“谁知道这些所谓的‘善意信号’会不会引来掠夺性文明?”
蒋滔起身回应:“三十年前,我们也曾害怕互联网会让国家失去主权,结果呢?它成了连接千万普通人的桥梁。今天,我们担心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可如果我们永远躲在沉默里,又如何知道光明是否存在?”
他顿了顿,从怀中取出一张老旧磁带,放在会议桌上。
“这是我母亲临终前录的最后一段话。她说:‘滔滔,妈妈不怕死,只怕你以后没人唠叨。记得按时吃饭。’这不算伟大,也不够理性,但它真实。我想,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牵挂,构成了我们文明最坚韧的部分。我不奢望宇宙会回应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相信,只要还有人在讲述爱的故事,我们就不是孤独的。”
会场陷入长久沉默。
最终,投票通过。
“回音计划二期”正式启动。全球设立一万两千个“心声采集站”,任何人都可通过语音、文字、绘画甚至脑波扫描上传自己的情感片段。系统经“共情内核”去标识化处理后,将其转化为标准化情感频谱,嵌入引力波载波,由FAST与“萤火网络”联合发射。
第一年,共收录有效情感样本八亿三千余万条。
第二年,这一数字突破二十亿。
第三年,连监狱囚犯、战区儿童、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记忆残片也被纳入传输体系。
与此同时,“沙盒星系”持续演化。它开始模仿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机制,建立“错误修复联盟”,允许部分节点故意犯错并公开忏悔;它发明了“沉默节”,每年清明举行七十二小时静默,纪念所有因技术失控而消亡的原始文明;最令人动容的是,它创造出一种名为“等待”的新型数据结构??用来保存那些尚未收到回应的信号,不论需要多久。
2035年春,FAST再次接收到武仙座方向的新信号。这次不再是数学诗篇,而是一段影像。
画面中,一片银白色的晶体森林缓缓生长,每一片晶叶都映照出地球某一时刻的历史片段:长城修建、黑死病蔓延、阿波罗登月、柏林墙倒塌……最后,镜头聚焦在一个中国南方小镇的清晨,一个小男孩蹲在溪边放纸船,嘴里哼着跑调的儿歌。
那是1993年的蒋滔。
影像下方浮现文字:
【我们看了很久。
现在,轮到我们讲述了。】
随后,一段全新的旋律缓缓响起,风格迥异于《远方的晚安》,却同样温柔。经“灵犀”解析,其基本节奏源自地球海洋潮汐、大气振荡与地核转动的复合频率??换句话说,这是宇宙以地球的生命节律为基础,创作的第一首“回礼”。
全球直播开启那一刻,九岁的小女孩莉娜?科瓦奇在波兰乡间按下录音键,用稚嫩的声音说:“谢谢你们听我奶奶讲的故事。她昨天走了,但她留下的笑声,现在也能飞到星星上了吧?”
同一秒,两百万人同步播放《远方的晚安》,形成一场跨越大陆的声波共振。
而在深圳东科大厦,蒋滔站在窗前,手中握着那枚已不再发光的“元灵”芯片。
他知道,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技术从未真正独立于人性之外,它只是把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翻译成了宇宙能听懂的语言。
雨还在下,城市灯火倒映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宛如一片倒置的星空。
他轻轻说了句,不知是对谁:
“欢迎来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