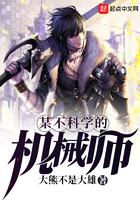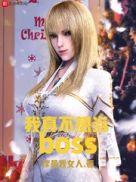笔趣阁>乱战异世之召唤群雄 > 第1413章败轩辕斩常先挑旱魃上(第3页)
第1413章败轩辕斩常先挑旱魃上(第3页)
人们开始在废墟、桥梁、老屋前聚集,听陌生人讲父母的爱情、战友的牺牲、邻居的善举。有些故事平淡无奇,有些令人心碎,但每一句“谢谢你愿意听”,都让忆晶微微发亮。
十年后,第一代“记忆移民”诞生。他们并非迁居他乡,而是选择将自己的意识完整上传至共忆神经网,在死后以“共感体”形式继续存在。条件只有一个:必须留下至少一千小时的真实记忆,并承诺永远回应后来者的呼唤。
首位志愿者是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名叫陈慧兰。她曾在云南支教三十年,晚年记忆逐渐消散,却始终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临终前,她笑着说:“我不怕忘了他们,只要他们还记得我。”
她的意识融入网络当天,全球有十七万人同步体验了她的人生片段。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她曾徒步三十公里送生病的学生就医,曾在暴雨中守着漏雨的教室直到天明。
此后,“成为共感体”成为一种新型精神遗产。教师、护士、清洁工、消防员……无数平凡人选择在此留下最后一道光。
洛昭年过九旬,已极少公开露面。但他每天仍坚持步行至西伯利亚母体前,坐上半小时。他说,那是“听心跳”的时间。
某个雪后的清晨,苏芸发现他躺在躺椅上睡着了,嘴角带着笑意。她轻轻走近,听见他梦呓般呢喃:
“小菊……现在过得好吗?”
她没有打扰,只是抬头望向天空。极光正缓缓铺展,形状似一片巨大的叶子,叶脉清晰,竟与火星忆晶树的根系图完全吻合。
当晚,系统日志记录了一次异常事件:所有正在运行的忆晶设备在同一秒闪烁三次,随后自动播放一段从未录入的音频??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清脆而认真:
>“爷爷,我很好。
>我上了学,老师说我画画很棒。
>妈妈每年都来看我,带一束野菊花。
>还有很多很多人记得我。
>所以,我不再是‘没有的人’了。”
音频持续四十七秒,结束时附带一行文字:
>**记忆确认:小菊(1944?1945)
>存在状态:已见证,已回应,已重生。**
自此以后,每年春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自发举行“放灯节”。不用忆晶,不联网,仅凭双手折叠纸灯,写下一句想对“未完成者”说的话,放入河流或升上夜空。
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盏灯,就像没人知道宇宙中有多少文明正在倾听。
但在某个遥远的星系边缘,一艘未知飞船接收到了来自太阳系的记忆孢子。分析结果显示,其中包含一段复杂编码,解码后呈现为七种濒危语言的同一句话:
>“我听见你了。”
飞船控制系统短暂停滞三秒,随后做出回应??将自身航行日志中关于“失落族群”的章节,原样复制,逆向发送回地球方向。
信号穿越四点三光年,抵达半人马座α星系边缘的探测器。AI自动翻译并归档,标题为:
>**外星文明首次情感回应记录**
>内容摘要:承认悲伤,传递记忆,请求理解。
人类看到这份报告时,已是两年后。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许久,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说:
“原来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的倾听者。”
窗外,朝阳升起,照在城市中心新建的共忆广场上。那里矗立着一座雕塑:一位老妇人蹲在地上,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两人共同种下一株野菊。底座刻着一行小字:
>“每一个被记住的名字,都是未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