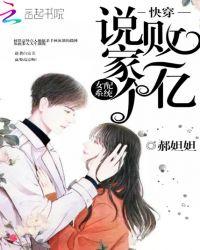笔趣阁>逍遥四公子 > 第1943章 一个女婿半个儿(第3页)
第1943章 一个女婿半个儿(第3页)
遂下旨:赦免所有流民罪籍,准其定居垦荒,赐田免税五年,并在全国推行“守望学堂”制度,每州设一所,专收寒门子弟,课程必修《守望录》。
消息传来,南疆营地万人欢腾。老人却在庆功宴上悄然离席,独自登上孤峰。夜风凛冽,他取出那只随身多年的铜铃,轻轻摇动。
“叮??”
铃声清越,穿透云雾,仿佛回应着千里之外归途镇的井光。
他望着星空,低声说道:“阿砚,你看见了吗?你的‘善’字,已经长成了森林。”
忽然,空中掠过一群信鸽,羽翼划破寂静。其中一只落在他肩头,爪上绑着一张极小的纸条。他展开一看,是小满的笔迹:
>“先生:
>我已成为听铃书院最年轻的轮值记事人。
>昨日我去探访一位老兵,他告诉我,当年替我爹挡箭的那位士兵,名叫陈默。
>他没有战死,而是重伤退役,靠打铁维生。
>我找到他时,他正在为村学打造课桌。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有人曾为我点亮过一盏灯,我现在只是把它传下去。’
>我哭了。
>原来,善良真的会循环。
>
>我想告诉您??
>铃声从未停止。”
老人看完,将纸条贴在胸口,闭目良久。
然后,他解下腰间铜铃,挂在峰顶一棵枯树上。风吹铃响,声传四方。
他知道,自己已无需再走太远。因为此刻,在北方的战场边缘,在南方的渔村码头,在西部的沙漠绿洲,已有无数人在讲述这些故事,在传递那份温暖。
十年后,归途镇更名为“仁州”,成为天下学子朝圣之地。而南疆营地发展为新城,名为“归南”,意为“归来之南”。两城之间,沿途设九十九座驿站,每站皆挂铜铃,每逢风起,铃声相连,绵延千里,宛如一条无形的血脉。
苏萤晚年定居归南城,主持全国“心光诵读团”,培训盲人教师三千余名。她在八十岁寿辰那日,当众宣布:
“我从未见过林隐先生的模样,但我听过他的脚步声,闻过他衣袖间的墨香,感受过他递给我的那根乌木杖的温度。他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光明,不在眼睛里,而在心里。”
又三十年,世间已无“林隐”传说,唯有《守望录》代代相传。某年春,仁州孩童在老井边玩耍,忽见水中浮现一行新字:
>“铃声将歇,然火不灭。
>若你心中尚存一丝暖意,
>请为陌生人撑一把伞,
>或教一个孩子写下一个‘善’字。
>这便是我对世界的最后请求。”
>
>??林
孩子们纷纷回家,取来雨具与纸笔。当天傍晚,一场春雨落下,整座仁州城中,无数人默默为路人遮雨,无数家庭点亮灯火,教子女写下人生第一个“善”字。
而在雪山深处的茶棚遗址,多年未曾有人迹。唯有每年清明,当地牧民总会发现??炉膛中有余温,案上有一碗清水,檐下铜铃微微晃动,仿佛刚刚有人离去。
风起时,似乎还能听见那首古老的谣曲,在天地间轻轻回荡:
>“雪落无声,心有回响,
>谁在远方,摇动铃铛?
>不问姓名,不求回望,
>只愿人间,处处是归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