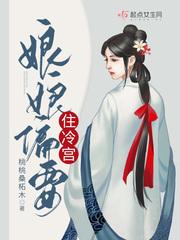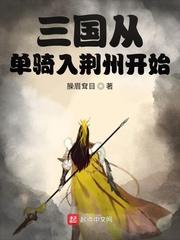笔趣阁>毫末生 > 第4章 红紫乱朱(第1页)
第4章 红紫乱朱(第1页)
诸郡县上报漕运开支一项,与御史大夫统合历年朝中所废钱粮的奏折,同一天摆在阴素凝的案头。
如此大事,本该在朝会上,经由皇帝颁布旨意。
阴素凝向来算得上本分,就算皇帝诸事不理,但大事都会经由他的手和嘴。
这一回一反常态。听闻两本奏折放在阴素凝面前时,皇后娘娘凤颜大怒。即刻命漕尉李崇清为漕运总督,彻查郡县数目不符,亏空钱粮一事。
次日卓亦常返京面圣,再呈《江淮漕运疏》,痛陈漕运沿途郡县多年来贪墨国库划拨银两粮草,治水疏惫,以致运河堰塞。
此事由来已久,往年风调雨顺时看不出来,近年开春连降豪雨,多年积弊就成了大患。
皇帝浑浑噩噩,仍是满脑子做着长生美梦。
朝堂中鸦雀无声,静了两炷香之久,传话太监才从帘后转出。
这一回他不再是轻声耳语,而是递了本折子。
皇后娘娘昨日已大怒过一回,朝臣们见此情状,知娘娘已有所准备。
皇帝只展开奏折随意扫了一页便不耐烦地合上,道:“就依皇后的意思办吧。”
一句话,大宋国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太监将奏折上的内容宣读一遍,条条在理,挑不出毛病来。
然忠直有志者大感失望,事关国运的大事,皇帝入过家家般儿戏。
但幸好有位贤良又长于理政的皇后,大宋国还能苦苦支撑。
至于那些近半年多来经阴素凝亲手提拔的年轻官员,更是愤愤不平。
皇后娘娘呕心沥血,新锐官员群策群力,皇帝却是这般态度。
整个大宋国三百年基业,在皇帝眼里就像一张染了墨滴的废纸,不值一文,随手可弃。
当日朝会,因卓亦常边关破敌有功,加封兵部侍郎,总督西北兵马。
因西北兵力,钱粮等空虚,暂留京城整顿兵马粮草。
卓亦常奏请遴选左右千牛卫大营等包含禁军中的精锐,抽调三成随赴西北,亦获恩准。
朝会上点起的一把火,很快在整个大宋国延烧。沿着涛涛运河,这把火点燃了沿途所有郡县,一路烧向新郑。
七日之后的大朝会上,新郑尹率先落马。
漕运一路通往京城,没有新郑尹里应外合,事不可行。
可当大理寺拿人,御史台公布罪责时,才真正让朝臣们一个个战战兢兢。
这位倒霉的新郑尹罪责中最重的一条,并非贪墨一罪,而是贩售私盐。
自追查漕运亏空一案,挖出私盐案,朝中无人不悚惧无比。
柴米油盐酱醋茶,私盐虽是杀头大罪,利润丰厚,哪个达官贵族不沾点?
于是百官噤声,无有提出异议者。
直到此时,齐开阳才发现阴素凝前期的用人无不伏走千里。
京中的大理寺,御史台,再到郡县的漕运总督,正是阴素凝在各个角落提前落子。
待这张大网打开,每一个绳结都心向于皇后,如臂使指。
这些办案的年轻官员各个奋勇争先,精神百倍,唯恐落于人后,错过了难得的机遇。
一切按着阴素凝的构思在顺利推进,可皇后娘娘轻锁的眉头始终未能舒展。
“有时候机会出现了,你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踏上一步,准备殊死一搏,准备和老天斗上一斗。在没有结果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还是万劫不复!”
齐开阳理解这种担忧。出山后历经多次险死还生,更懂得这种感受。
白日的批阅奏章,齐开阳将阴素凝抱在怀里,偶尔给出些异想天开的意见,大多数不可用。
偶有灵感,阴素凝便即采纳。
可这些细节并不能改变全局,阴素凝的眉头仍是轻锁。
到了夜间,齐开阳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翻江倒海似地搅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