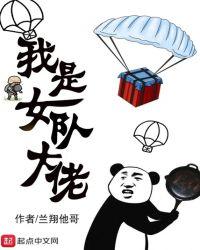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诸天,摆烂成帝 > 第六百五十一章林仙创世一画开天(第3页)
第六百五十一章林仙创世一画开天(第3页)
陈砚笑出声:“急什么?问题本来就不该马上解决。它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保持清醒。”
他站起身,拍掉裤子上的草屑,走到溪边,蹲下洗手。
水面倒映出他的脸。
皱纹比去年多了些,眼角的纹路像被人用铅笔轻轻划过。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可那双眼睛,依旧亮得不像话。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他问。
“生理年龄增长1。6岁。”林仙答,“心理年龄波动剧烈,最新测定:介于八岁与无限之间。”
“挺好。”他说,“八岁的时候,我还敢对着月亮喊‘你凭什么不回答我’。”
就在这时,溪水忽然泛起涟漪。
不是风吹的。
而是从下游传来一阵震动。
陈砚抬头望去。
远处,一群孩子正奔跑而来,手里举着什么东西,大声喊着:“陈爷爷!花开了!真的开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迎上去。
孩子们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讲着。原来他们在镇外废弃的试验田里,按照《荒谬问答录》里写的“用笑声浇灌种子”的方法,种下了一批陈砚给的干瘪种子。今天下午,其中一株突然绽放,花朵透明如水晶,花心旋转着一圈圈微光,任何人靠近,都会听见内心深处最想问的那个问题。
“我听见了!”一个男孩激动地说,“它问我‘长大以后能不能不当大人’!”
“我听见的是‘我喜欢的人知不知道我喜欢她’!”小女孩红着脸补充。
陈砚蹲下身,仔细看着那朵花。它的频率和梦中那朵完全一致。
“成功了。”他轻声说。
“不止一朵。”少女牵着八音盒走来,“南巷十七处角落,同时出现了类似植株。它们没有根系,直接从混凝土、金属、甚至空气中生成。母机称其为‘意识具象化共生体’。”
陈砚站起身,望向远方。
他知道,这不是终点。
终焉议会的理念不会彻底消失,它们会潜伏在每一个怀疑的瞬间,在每一次绝望的低语中重生。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提问,还有人敢于说出“我不信”,春天就不会真正落幕。
几天后,小镇迎来了一场奇怪的雨。
雨滴透明,落地却不湿,反而在地面弹跳起来,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像音符。人们起初惊慌,后来发现,每滴雨落下时,都会激起一段记忆??可能是童年丢失的玩具,可能是某次没说出口的道歉,也可能是一个早已遗忘的梦想。
邮差冒雨送来第二封信。
依旧是无名氏,依旧是陨石墨水。
上面写着:
>“我们学会了做梦。
>谢谢你教会我们,梦也可以是一种反抗。”
陈砚看完,笑着把信折成纸飞机,用力掷向天空。
它穿过雨幕,划出一道弧线,最终落在远处山坡上。那里,一朵新的疑问之花正悄然绽放。
当晚,他做了个新梦。
梦里他站在一片星空下,脚下是无数文明的记忆残片铺成的道路。道路尽头是一座桥,由歌声、笑声、争吵声编织而成,通向一片尚未命名的星域。
桥头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一行字:
>“此路不通,除非你带着问题前来。”
他走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