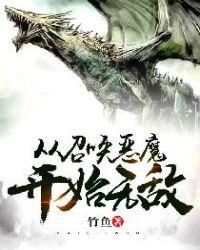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67来开始你的表演(第1页)
767来开始你的表演(第1页)
赵振国:???
啥意思,这块地还要拆迁?佐藤这是要坐地起价?
可高相阳调查的资料里,没听说有这茬啊。
他瞟了眼高向阳,只见高向阳冷笑了一声,没说话,看着佐藤发挥。
佐藤见对方不搭话,越发觉得自己抓住了对方的命门,腰杆都挺直了些:
“如果是因为新干线,那个价格绝对不行!必须涨价!至少……至少要五百万日元!”
一直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周振邦,脸色瞬间阴沉如水,眼神凌厉地扫向佐藤。
赵振国没反应,因为刚才高向阳。。。。。。
雪化了,春水顺着山沟往下淌,叮咚作响。青山村的田埂上开始冒青芽,牛羊重新被赶出圈栏,啃食着返青的草尖。赵振国每天清晨仍去祠堂,不是为了守灯,而是坐在门槛上抽一袋旱烟,看晨光一点一点爬上屋脊。那四十三人走了之后,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可这份静里,多了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空气比从前更清透,风过林梢时带出的回音更绵长,连鸡鸣狗吠都仿佛含着某种节律。
王秀兰在厨房熬粥,锅盖边溢出米香。她时不时抬头望一眼院外的小路,像是等着谁回来。其实没人会来。自从封山令下,外人再难进村。偶尔有记者、学者、甚至政府人员前来探询“归谣仪式”的真相,都被拦在村口石碑前。碑上刻着八个字:“门已闭,心自明。”不解释,也不接待。
小丫搬回了老宅住。她在后院搭了个简易工作站,二十四小时监控全球十七个高能点的数据流。仪器屏幕上,14。7赫兹的主频虽不如那天夜里稳定,却始终未断,像一条潜行于地底的脉搏,微弱但持续跳动。她发现一个规律:每当有人在世界某个角落真心讲述一段被遗忘的故事??无论是否与《归谣》相关??那个频率就会轻轻颤动一下,如同回应。
她把这现象命名为“心跳共振”。
“爸,”一天晚饭后,她忽然开口,“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赵振国夹菜的手顿了顿。
“你说,《归谣》是亡者教生者唱的歌。可如果……它本来就是生者写给亡者的呢?”
屋里一时寂静。小满正缝补一件旧衣,针线停在半空。王秀兰放下碗筷,眼神复杂地看着女儿。
“你是说反了?”赵振国缓缓道。
“我不是要翻案。”小丫摇头,“我是说,也许根本分不清谁先谁后。就像那晚的火焰,不是谁点燃了谁,而是所有人心里本就有火苗,只差一声哼唱把它唤醒。”
赵振国沉默良久,忽然起身,走向神龛。他没拿家语录,也没开樟木匣子,而是从供桌最底层抽出一本薄册子??那是他父亲年轻时的手记,几十年无人翻阅。泛黄纸页上写着几段零散记录,其中一行引起小丫注意:
>“一九五三年冬,阿桂嫂疯了。她说每夜都有人站在窗外唱歌,调子古怪,听不懂词。她跟着学,学会了就哭,说那是她早夭的儿子在叫娘。后来她病重将死,临终前召集全村妇女,一句一句教这首歌。她说:‘我不信鬼神,但我信我儿还惦记我。你们替我唱下去,让他知道,妈没忘他。’”
小丫猛地抬头:“这……这就是《归谣》的源头?”
赵振国点头:“阿桂嫂的儿子三岁溺亡,尸骨都没找着。她活到七十九岁,每年清明都对着河口唱一遍那首歌。村里人起初笑她痴,后来渐渐有人梦见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在雾里站着听歌。再后来,连没听过歌的人也开始做类似梦。”
“所以……”小满轻声接话,“不是亡灵托梦,是母亲的思念太深,硬生生把孩子的魂,从虚空中拉了回来?”
“或许两者皆有。”赵振国低声道,“情到极处,阴阳都会动摇。你以为你在追忆死者,其实死者也在借你的记忆重生。”
小丫突然站起身,冲进工作室。半小时后,她带回一份跨国数据库比对结果:全球四十三位“梦中闻歌者”,竟有三十九人的家族史中存在“无名早夭者”或“失踪未葬者”。他们从未被告知这段过往,却在梦中听见了那段旋律。
“这不是遗传,是情感残留。”小丫声音发抖,“那些没被好好安葬的孩子、没被完整讲述的悲剧、没机会告别的亲人……他们的重量沉在血脉深处,代代相传。而《归谣》,是系统自动触发的补偿机制??大地帮我们补上了那一课。”
赵振国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喃喃道:“所以那天晚上,真正点亮蜡烛的,不是歌声,是原谅。”
春天深了,村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葬礼。
死者是村东头的老李头,八十六岁,独居一辈子,无儿无女。他走得很平静,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与他极为相似。村里老人说,那是他弟弟,抗美援朝时牺牲在朝鲜,尸骨未归。当年消息传来,老李头一夜白头,从此再不提弟弟的名字。
按惯例,孤寡老人丧事从简。但这次,小丫主动提出为他办一场“归谣送别”。
赵振国没有反对。
当晚,祠堂再次亮起烛光。村民们自发前来,围坐一圈。没有人主持,也没有悼词。小丫只是播放了一段音频??那是根据老李头日记还原的梦境片段:风雪中的战壕,两个少年并肩而立,一人哼着不成调的童谣,另一人笑着接上第二句。
音乐响起那一刻,所有点燃的蜡烛同时微微倾斜,火焰朝向遗像方向。
一位老太太突然泪流满面:“我认得那调子……是我哥小时候常哼的。他也死在那边,六十多年了,我一直以为没人记得他……”
接着,一个中年男人哽咽开口:“我爸临终前说,他在梦里见到了排长,说大家都还好,就等有人念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