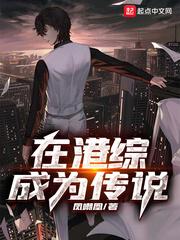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 > 第476章 这一年的最后一日(第3页)
第476章 这一年的最后一日(第3页)
信的内容很简单:
>“志清,姐姐对不起你。当年不该劝你别顶撞干部。你走后,我每天都在后悔。如今我快不行了,只想让你知道??你说得对,错的是我们这些沉默的大人。”
艾米丽含泪接过信,当场宣布增设“未寄之声”互动展区,允许参观者现场录制并留存自己的记忆。
回到国内后,她与陈砚、苏晓三人彻夜商议未来规划。他们决定将“诚言学堂”升级为跨代际对话平台:每学期举办“两代人共学周”,邀请学生与长辈同堂听课、共同创作;设立“沉默者奖”,表彰那些晚年终于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普通人;并推出“言种计划”,资助偏远地区教师开展记忆教育实验。
首个试点落在云南山村小学。那位曾下令焚粮的老人成了最受欢迎的讲师。孩子们围着他,听他讲如何从理想青年变成执行机器的过程。有个小男孩举手问:“老爷爷,那你现在快乐吗?”
老人愣住,良久才回答:“只有当我开始说实话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像个活人。”
课程结束那天,全班合作完成了一本手绘书《错误手册》。封面画着一株被火烧过的树,树根深处钻出新芽。扉页写着:“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假装没发生。”
这本书被送往诚言学堂收藏,编号001。
而在城市另一端,那位曾在文革中举报老师的退休女教师主动联系了《家?春秋》栏目组,提出愿意走进校园,面对面与学生交流。“我不想躲在镜头后面道歉。”她说,“我要看着孩子们的眼睛,亲口告诉他们:我错了,但我愿意改正。”
她的第一场讲座座无虚席。结束后,一个女生站起来说:“老师,谢谢您。因为我爸爸也是告密者,他从来不说那段事。今天听了您的话,我想回去告诉他:说出来吧,我们都准备好了听。”
教室里响起掌声,有人低声啜泣。
春天就这样悄然蔓延。不是以雷霆万钧之势,而是以千万次轻声诉说的方式,渗透进这个曾习惯沉默的国度。
某日黄昏,林小禾独自回到归名书院遗址。工地已初具轮廓,环形剧场的地基铺好,三百块刻名石板整齐排列。她蹲下身,指尖抚过外公的名字,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是陈砚。
“你知道吗?”他站在她身旁,望着西沉的夕阳,“我最近常做一个梦??梦见这所学校建成后,每天早晨都会有孩子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读他们写下的真实。没有修饰,没有顾忌,只是纯粹地说出心里的话。”
林小禾微笑:“那一定很吵。”
“是啊,”陈砚也笑了,“但那才是活着的声音。”
风吹过海棠树苗,嫩叶沙沙作响,宛如回应。
当晚,林小禾写下一篇日记:
>“今天我们总说‘铭记历史’,好像记忆是一件沉重的石头,必须背负前行。可我现在明白了,记忆其实是一粒种子。它不压弯你的脊梁,反而让你生出新的枝干。
>
>外公没能看到这一天,但他种下了第一颗火种。
>
>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肯开口说一句真话,就是在浇水,就是在护光。
>
>春天从来不属于某个时刻,它属于所有不肯闭嘴的灵魂。
>
>此册不闭,因言未止。
>
>此花常开,因根未断。”
合上日记本,她抬头望向窗外。星空澄澈,那朵海棠形状的星图静静闪烁,仿佛在低语:
>“你们已经说得够久了。
>
>现在,轮到我们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