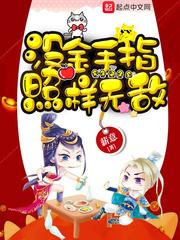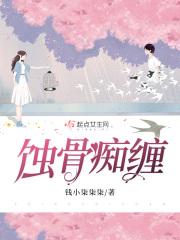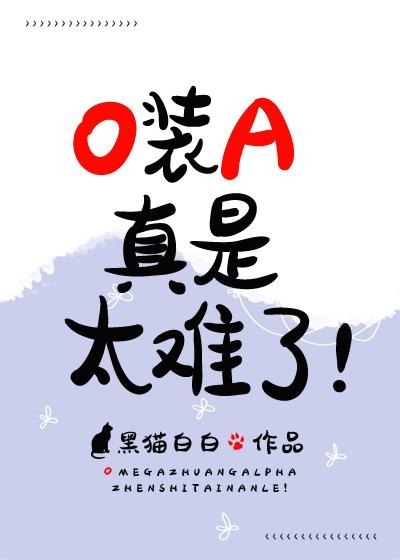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 > 第477章 没应也没动(第2页)
第477章 没应也没动(第2页)
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临别时,沈云卿将那张照片塞进林小禾手中:“送给你。不是为了纪念过去,是为了提醒未来??当一个人开始否认自己的记忆,自由就已经死了。”
回到家中,林小禾将录音上传平台,并附上一句留言:“她说她骗了自己四十年。可今天,她终于对得起那群站在雪地里的年轻人了。”
这条动态迅速被转发数万次。许多网友留言称,自家长辈也有类似经历:有父亲藏了三十年的手稿,只敢在醉酒后念给儿子听;有母亲临终前反复叮嘱女儿“不要提爷爷的名字”,直到死后才从遗物中发现一封未寄出的平反申请书。
就在当晚,陈砚来电,声音罕见地激动:“小禾,基金会收到一笔匿名捐赠??整整五十三本手抄日记,时间跨度从1958到1976年。捐赠人只留了一句话:‘这是我父亲用生命记住的事,现在轮到我来交出去了。’”
“能看内容吗?”林小禾问。
“可以。全是钢笔小楷,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最关键的是,他记录了三年困难时期某县真实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还有干部如何虚报产量、克扣救济粮的过程。这些数据,官方档案至今未公开。”
林小禾心头一震。
“我已经联系了几位可信的历史学者做交叉验证。”陈砚说,“如果属实,这将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批民间史料。”
“是谁捐的?”她问。
“不知道。包裹是从西北一个小县城寄来的,寄件人信息全是化名。但我们查到当地邮局监控??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右腿微跛,走路时总扶着墙。”
两人沉默片刻。
“你觉得……他会是下一个站出来的人吗?”林小禾轻声问。
“也许不会。”陈砚说,“但他已经做了比说话更勇敢的事??他选择了信任。”
挂断电话后,林小禾翻出外公的手稿,在最新一页写下:“真正的勇气,有时不是呐喊,而是递出一只颤抖的手,把真相交给陌生人。”
几日后,苏晓传来消息:“声音档案馆首批数字化工程完成,共收录口述史1273段,文字转录逾八百万字。我们开发的情感标记系统已识别出高频词??‘后悔’‘隐瞒’‘不敢说’位列前三。”
她顿了顿,又补充:“最让人难过的是,超过六成讲述者提到‘孩子问起那段历史时,我只能摇头’。”
林小禾看着屏幕,久久无言。
当天下午,她接到母亲电话:“村西头李婶走了,九十岁,走得安详。她孙子收拾遗物时,在炕席底下发现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她年轻时写的诗,还有几张泛黄的信纸??是她未婚夫在劳改农场写的。”
“他说什么?”
“说他每天都在背《滕王阁序》,怕忘了汉字;说他梦见家乡的稻花开得漫山遍野;最后一封信写着:‘若我回不去,请替我看看春天。’”
林小禾闭上眼。
“她孙子问我,能不能把这些放进诚言学堂的展览?”
“当然能。”林小禾声音哽咽,“而且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周后,“未寄之声”展区正式开放。展厅中央设有一面“信墙”,悬挂着百余封从未寄出的信件复制品。灯光柔和,每封信旁配有语音朗读。参观者戴上耳机,便能听见那些跨越时空的声音:
一位母亲写道:“儿啊,娘不该让你去参军。他们把你名字刻在烈士碑上时,我才知道你死在无人知晓的山谷里。”
一位知青写道:“阿芳,我烧了你的信。不是不爱,是怕连累你。如今我儿娶妻,我才敢写下这句:我一直记得你穿着蓝布裙站在河边的样子。”
最角落处,静静躺着程志华那封未曾寄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爸,我没偷粮食。我只是想带回两斤米,给发烧的妹妹煮碗粥。他们说我犯了罪,可我不懂,饿是不是也是一种罪?”
无数人流泪离开展厅。有人跪在信墙前轻声说:“对不起,我们迟到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