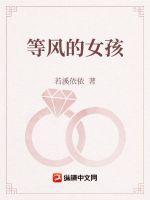笔趣阁>[红楼]吾皇黛玉 > 200210(第27页)
200210(第27页)
那少年一见这情形,便站住了,将臂弩收在身后,笑道:“公主在解闷儿呢,我只当你吃了酒睡觉了。”
诺敏将宝玉肩头的弩箭猛地拔出,痛得他青筋暴跳,嘶叫起来。
少年瞥了一眼那个被公主压在地毯上的男人,瞬间神色有些异样,很快又高昂起了下巴,冷漠地向那只无处可逃的小鹿射了一箭。
“思勤,你的箭术连十岁的哲布都比不上,再栽了牙,也没处补去。还是跟你母亲学绣花去吧。”
诺敏没好气地将带血的箭矢,扔回他脚下。
少年抿紧了嘴,扭脸出去了。
不一会儿,他沉着脸,走进了另一个较小的毡帐中。
一个头戴姑姑冠,身披绸袍年轻的妇人,正在低头做针线,听到儿子的脚步声,抬眸笑道:“兰儿,回来了。”
“娘,我瞧见宝叔了,今儿他被瓦西里的人俘过来,而今成了诺敏的玩物。”
这母子二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前荣国府二房的大奶奶李纨与重孙嫡男贾兰。
李纨手里的针顿了顿,拉过儿子的手说,“早不是一家子了,他是好是歹,不与我们娘俩相干。别人问起来,照实说就是了,只别露声色,由人说嘴去罢。”
贾兰点了点头,他母子从贾府回到李家,又从李家来到鞑靼,从来都是隐忍低调,精打细算,在夹缝中求生存。
只是如今诺敏的母妃下降给岱钦,母亲的绣帐鸳衾,就再也没热过了。
幕天席地的草原,让他早知人事,可汗的比姬娜米拉的到来,直接夺走了母亲的丈夫,她将再次忍受寡居一般的寂寞岁月。
“娘,武英帝已经打过斡难河了,一旦鞑靼败了,我们就再无退路可走,要早做打算了。”贾兰忧心忡忡地说。
李纨也并不是随遇而安的性子,从前被压抑的性情,在草原上得到了宣泄,对于金钱与权力的渴望,也得到了满足。
她不甘心自己背弃故国,得来的地位与利益,被另一个女人给瓜分殆尽。
更不想再次沦为俘虏,被中原人口诛笔伐,在史书上落下遗臭万年的骂名。
李纨叹道:“我何尝不也这样思量了几个彻夜,如今瓦西里胜了一回,中原与鞑靼胜负难料。瓦西里若与诺敏成亲,娜米拉的气焰只会越嚣张。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早下手为强。”
“诺敏那个丫头,可不会乖乖成亲,我们得想个法子,帮她逃婚出去。”贾兰若有所思,想起被诺敏玩弄的宝玉,沉吟道,“或许这个锅应该让他背上。”
翰儿朵帐中,宝玉被诺敏生灌了几碗鹿血,根本招架不住这女人的霸道和强势,完全落入了她的掌控之中。
他被困锁在铁链中惶然无措,一边是近乎屈辱的折磨,一边是近乎疯狂的快意,冰火交袭在他身上,让他魂不附体,神飞天外。
一直悬挂在脖子上的通灵宝玉,被猩红的血污染,灵光不再,片片碎裂。
他恍然想起,从前在秦可卿房中,做的那场关于云雨的幻梦。
是了,他的一生从那时起,便堕入了迷津,为情所迷,久久未醒。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①
他终于记起了自己是谁,他不是那个行为偏僻,性格乖张的贾宝玉,也不是那颗愚顽不灵、贪恋红尘的破石头。
他是神瑛,赤瑕宫中的侍者,而不是主人。
赤瑕宫,是主人寄放恋心的神殿,以五色石玉为体,以绛珠仙草为心。
亿万斯年,不曾忘却的情愫,却因为他对绛珠仙草心生怜意,以甘露浇灌,坏了因果,误入尘缘。
他的主人,是开辟天地的鸿蒙。
第209章吾皇黛玉第两百零九回
柳五儿失鞋草坡上,李夫人拦马牙帐前
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柳五儿晨起揽镜梳妆时,就知道了答案。
丈夫英吉让她过上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日子,一点儿活计都不让她干。洗衣做饭他都大包大揽过去,就连针线缝纫都舍不得让她动手,也一并抢走做完。
但凡有点空闲,英吉就带着她出门逛街、踏青赏景、泛舟游湖。
神医王君效说,她的病不过是年幼失于调养,脾胃失和,只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保持心情舒畅,多到户外走动,不出半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