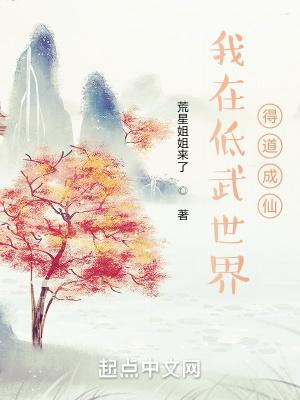笔趣阁>捞尸人 > 第四百五十二章(第3页)
第四百五十二章(第3页)
“倾听的代价。”沈清梧说,“你接受了所有被忽视的声音,也继承了它们带来的痛苦。这颗‘缄默种’会在你心中生长,每逢有人选择沉默,它就膨胀一分。终有一日,它将吞噬你。”
“那怎么办?”
“传播倾听。”她微笑,“让更多人学会说,也学会听。当世间回响足够多,缄默种便无处扎根。”
话音落下,沈清梧的身影开始消散。
“等等!”陈知秋伸手,“我还想知道母亲的事!”
“她不是候选人。”沈清梧回头,眼中含笑,“她是前任‘听者’。她放弃的不是职责,而是执念??她发现,真正的救赎不在渡亡魂,而在唤醒生者。所以她选择做一个普通母亲,用二十年光阴教你如何倾听一个小女孩的恐惧、孤独与渴望。”
“而现在……”她身影几近透明,“轮到你教这个世界了。”
晨曦初露,第十桥隐入虚空,唯有第九盏灯依旧明亮。陈知秋拖着伤躯回到梅园,发现供桌上多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背面写着:
>“知秋,
>我不敢做英雄,
>所以做了你的耳朵。
>现在,换你了。”
她紧紧抱住照片,泪如雨下。
数日后,村里办起了“说话节”。每月初七,家家户户在河边放灯,写下平日说不出口的话。孩子们学会了倾听老人的故事,年轻人主动向父母道歉,连一向冷漠的渔夫也开始哼起亡妻最爱的小调。
陈知秋依旧教书,但学生们总觉得她越来越“模糊”??有时叫她“陈老师”,她会愣一下才反应过来;有时交上作文,她批改的评语竟是几十年前流行的文字风格。
只有她知道,自己的记忆正在缓慢流失。
但她不再恐惧。
每当夜深人静,她便坐在河岸,取出青铜笔,在纸上画下今日听见的话语。笔尖过处,冰晶凝结成微型剧场,重现那些感人瞬间。她把这些“冰戏”送给孩子们当礼物,让他们在寒冬里看见温暖。
一年后的春天,她发现自己已经记不清自己的生日。
又过半年,村里新人教师接替了她的课。老村长看着空荡的校舍,叹了口气:“陈老师啊……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吧?”
她站在人群之外微笑。
当晚,她最后一次走上光桥,将青铜笔插入桥心。笔身碎裂,化作万千光点,融入九灯之中。而那支笔尖,则坠入河底,扎进第十桥基石,成为永恒的锚。
她转身离去,身影渐淡。
临别前,她在岸边石碑空白处,用手指轻轻划下最后一行字:
>“我不是谁的延续,
>我是我所听见的一切。
>若你呼唤,我仍在。”
风吹过,字迹迅速被苔藓覆盖。
十年后,梅园小学新建图书馆,馆员整理旧物时,发现一本无名手记。翻开第一页,只有一幅冰晶绘成的画:一位女子站在桥上,手中握笔,周身环绕无数发光纸船。画旁小字: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不敢说、来不及说、说不出口的人。
>你们的声音,曾照亮一个人的生命。
>而那个人,曾照亮一座桥。”
窗外,春风拂过,七株寒梅再度盛开。花瓣飘落河面,自动排列成一行字,转瞬即逝:
>“我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