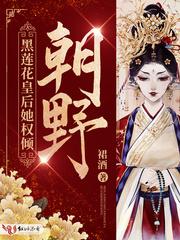笔趣阁>影视编辑器 > 第169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3页)
第169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3页)
苏宁当即提笔写信,命快马送往天津卫:“速改道登州,由海路进京,切勿登陆运河沿线城镇。我已命水师提督戚继光派战船接应。”
同时,他亲自入宫求见。
此时的嘉靖帝正在西苑炼丹房打坐,炉火映照着他枯槁的面容。
“陛下。”苏宁跪地叩首,“臣有本奏。”
“讲。”嘉靖闭目。
“严党虽除,国蠹未尽。今有确凿证据表明,部分边将与市舶官员勾结,长期走私军资出海,换取金银私肥囊橐。更有甚者,将倭寇缴获之火器重新流入边军,致使前线战力反降。”
嘉靖睁开眼:“何以为证?”
“臣已遣人追回原始航海日志,不日将抵京师。其中记载,近三年来,仅蓟州一镇,便通过走私获利白银百万两以上,而同期上报战功斩获,不足实际三分之一。”
嘉靖沉默良久,忽然问道:“牵涉何人?”
“陆炳麾下多名将领,均有往来账目。”苏宁直言不讳,“甚至……有人冒用陛下名义,调拨内库物资用于私贸。”
“放肆!”嘉靖猛然拍案,却又瞬间冷静下来,“你可知你说的话,足以诛九族?”
“臣知。”苏宁伏地,“但若不说,大明将亡于无声之中。”
殿外雷声滚滚,仿佛天地共鸣。
良久,嘉靖长叹一口气:“罢了……朕准你继续彻查。但记住,有些名字,不可点。”
“臣明白。”苏宁低头,“有些账,可以暂时不结。但痕迹,必须留下。”
退出丹房时,吕芳悄悄拦住他:“苏大人,皇上今日服了丹药后吐血了。”
苏宁心头一震。
这位沉迷长生的帝王,终究也是血肉之躯。他所畏惧的,或许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死后史书如何书写他的名字。
回到清账司,他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宣布一项新制度:**“双轨记账法”**。
即所有重要账目,必须同时记录于纸质账册与独立石碑之上,石碑埋于皇城地宫,非皇帝亲诏不得开启。
“我们要让百年后的史官知道,”苏宁站在庭院中央,声音坚定,“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数字,都是真实的。”
七日后,天津卫传来捷报:清账司船队安全抵达,所有证据完好无损。
同日,戚继光亲率水师护送,将船队直接驶入通惠河,直抵东便门码头。
当钱伯安捧着那本航海日记踏上岸时,围观百姓自发跪倒一片。
他们不懂什么审计、什么账册,但他们知道,有人在为他们讨公道。
当晚,苏宁将全部证据整理成册,命名为《海蠹录》,连夜送入宫中。
三日后,圣旨下达:
“着即成立‘海事专案司’,由翰林院侍读苏宁全权督办。凡涉及沿海走私、军资外流者,无论官职高低,一体严查!”
同时,陆炳被责令“居家反省”,其下属十余名将领被捕。
高淮闻讯欲逃,却被自家仆人绑缚送至衙门??原来那仆人正是陈九安排的卧底。
至于裕王?他在府中焚毁了一批信件,然后主动上表请罪,称“用人失察,愿受责罚”。
嘉靖帝批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一场滔天巨浪,似乎就此平息。
但苏宁知道,这才刚刚开始。
他在书房点燃一支香,望着袅袅青烟,低声自语:“父亲,我儿此去京城,不求显达,但求无愧于心……今日,我仍在路上。”
窗外,晨曦初露,照在清账司门前那块新立的石碑上。
碑文仅有一行字:
**“凡经手钱粮者,必留痕。天可见,地可鉴,心不可欺。”**
风拂过碑面,如一声悠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