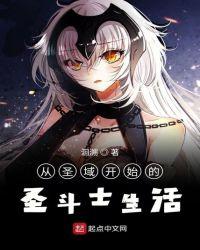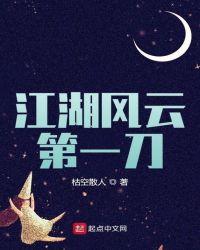笔趣阁>国潮1980 > 第一千六百五十二章 可怜虫(第2页)
第一千六百五十二章 可怜虫(第2页)
挂掉电话后,她抱着那只来自意大利的灯笼走到院子里。赵振国正在检查新装的防冻照明系统,见她来了,笑道:“洋娃娃也来凑热闹了?”米晓卉点点头,把灯笼挂在廊下,点燃蜡烛。火焰跳跃了一下,映出画中两个孩子的笑脸。
“你说,十年后的孩子们还会记得今天我们做的事吗?”她问。
赵振国放下工具,望着那盏微微晃动的灯:“记不记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还有人愿意接着点下去,这件事就没有终点。”
雨季来临前,林婉清完成了一项惊人发现。她在整理一批散佚于民间的民国乡村教育档案时,意外找到一份1937年的《战时流动讲学记录簿》。里面记载了一支由十二位教师组成的“烽火读书团”,在抗战爆发后辗转七个省份,沿途设立临时学堂,教授语文、算术与爱国常识。他们在山西某村停留半月,临走时留下一本手抄《孟子》,扉页写道:“书可焚,志不可夺;地可陷,学不可废。”
更令人动容的是,记录簿最后一页标注了每位团员的结局:七人死于空袭,三人失踪,一人被俘后宁死不降,仅两人活至新中国成立。而其中一位幸存者的名字,竟是李志远祖父的别名。
消息传到“墨香斋”那天,李志远正在备课。他接过复印件,手指微微颤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时,他闭上了眼睛,良久才低声说:“原来他一直没停下脚步。”
第二天清晨,他独自来到平遥明代义塾遗址,在那块出土的《兴学记》石碑前肃立良久。然后,他从包里取出一支毛笔和一方砚台,蘸墨挥毫,在宣纸上写下八个大字:“薪尽火传,志士不孤。”他将字幅贴在碑旁,点燃一支香,默默鞠躬三次。
当晚,“晨读联盟”发起“重走烽火路”特别行动。五十名青年传承人分五路出发,沿着当年“烽火读书团”的路线行走探访,每到一处便举办公益讲座、修复旧校舍、收集口述史。他们的背包里都带着一本复制版《战时流动讲学记录簿》,并在扉页签下自己的名字。
三个月后,第一支队伍抵达甘肃天水。在当地一所废弃小学的断墙边,他们挖出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竟藏着半本残缺的《千家诗》和一张泛黄的照片??正是那十二位教师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小字:“纵使山河破碎,亦要书声不绝。”
队员们当场跪地敬礼。领队拨通米晓卉的电话,声音哽咽:“我们找到了。他们真的来过。”
夏日炎炎,“承志园”的荷花池开满了花。米晓卉邀请当年参与“守常居”筹建的几位元老齐聚一堂,举行“五年回顾会”。会上,她播放了一段从未公开的影像资料??那是2018年冬天,周老先生弥留之际,在病床上最后一次讲述“守常居”的由来。画面中,老人气息微弱,却仍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怕死,只怕有些事没人接着做。只要还有一盏灯亮着,我就没真正离开。”
全场寂静无声。林婉清低头擦拭眼镜,赵振国握紧了拐杖,陈知微悄悄握住了米晓卉的手。
会议结束时,米晓卉宣布启动“种子计划”:面向全国招募一百名“文化火种员”,每人资助三万元,用于在当地创办微型书院、组织社区共读或开展非遗教学。申请条件只有一条??必须承诺连续服务至少五年。
“我们不再追求宏大叙事,”她说,“我们要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花。”
秋风吹起桂花瓣的时候,第一份“种子计划”成果报告送达办公室。云南大理的一位白族姑娘利用资助金,在自家院子办起了“松溪书屋”,每周六免费教村里孩子读诗写字。她寄来的照片里,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手中举着自制的树叶灯笼,笑容灿烂如阳。
而在内蒙古草原深处,一位蒙古族牧民建起“星空下的晨读角”。夜晚放牧归来,他便带着儿女坐在蒙古包前,用蒙汉双语朗读《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声音随风飘散,融入浩瀚星河。
冬至那天,全球二十四节气共读活动如期举行。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从漠河到三亚,从伦敦到悉尼,超过六百所学校同步诵读杜甫的《小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新西兰的小艾拉再次举起灯笼,对着摄像头大声说:“Springiscoming!”
阿富汗的晨读站里,孩子们用刚学会的中文齐声喊出:“春天来了!”
北极圈内的因纽特孩子则用拼音卡片拼出了“dōngzhìkuàilè”(冬至快乐),并把它贴在了帐篷门口。
米晓卉站在“守常居”的天井中,仰望着被灯笼染红的夜空。她忽然想起多年前周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灯不怕远,只怕无人点。”而现在,她分明看见,那一点微光,早已燎原成海。
雪又开始下了。但她知道,春天,真的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