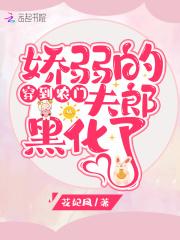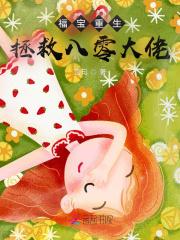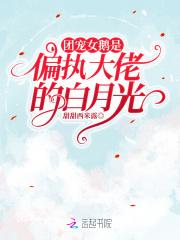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60章 为什么要在军事电影里找爱情(第3页)
第660章 为什么要在军事电影里找爱情(第3页)
>真正的倾听,始于尊重不说的权利。”
文章发布后,迅速引发热议。支持者称其“刺破了公益表演化的脓疮”,反对者则指责他“阻碍数字化教育进程”。一场关于“技术与人性边界”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一周后,教育部发文叫停部分地区强制学生直播的做法,强调“任何教育活动不得以牺牲学生隐私与心理健康为代价”。
与此同时,《大地之声2》正式进入制作阶段。林浩然决定加入一个全新环节??“沉默之声”特辑,专门收录那些选择不公开身份、仅愿留下声音的讲述者。他们中有遭受家暴的妇女、失业多年的工人、抑郁症患者、跨性别者……他们的共同点是:终于鼓起勇气说话,却又害怕被人认出。
为此,团队开发了一套语音变形技术,在保留情感质地的前提下模糊音色特征。每一首都标注:“此声匿名,但真实存在。”
专辑最后一首,是林浩然亲自选定的一段街头录音。地点在北京地铁十号线,时间是某个冬日凌晨五点。画面无人,只有环境音:列车进站的摩擦声、自动扶梯运转的嗡鸣、远处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是对着空气说话:
“老伴儿,今天我又梦见你了。你说想看颐和园的荷花,我没带你去,一直后悔。现在我每天都去一趟,拍下来放手机里,回家放给你听……你说奇不奇怪,明明你走了五年,我却觉得你还在。”
录音结束前,老人轻轻笑了下:“你看,我又?嗦了。”
林浩然把这首歌命名为《未寄出的情书》,并放在专辑末尾。他说:“有些话,注定没有收件人。但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抵达。”
春天再次降临,大理的声音档案馆主体完工。竣工仪式那天,全国各地来了上百位参与者??有当年第一批录音的孩子,有参与建设的志愿者,也有仅仅因为听过某段声音而专程赶来的人。
才让校长带着卓玛也来了。十六岁的卓玛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站在奠基碑前,轻声说:“三年前我在这里录下对阿妈的思念,今天,我想告诉她,我已经不怕提起她了。”
林浩然站在人群中,看着阳光穿过玻璃幕墙洒在展厅地面,照亮那一排排微型扬声器。它们像无数只耳朵,静静等待下一个声音的到来。
剪彩之后,他走上台阶,面对所有人说道: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馆?我说,因为它提醒我们:伟大不只存在于丰碑之上,也藏在每一个平凡人的呼吸之间。
我们收集的从来不是声音,而是人类如何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尊严的证据。
也许未来某一天,当某个孩子走进这里,听到百年前另一个孩子说‘我想活下去’,他会知道??
他并不孤单。”
话音落下,全场静默数秒,随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
当晚,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档案馆中央那面巨大的镜子终于安装完毕,镜面干净澄澈,倒映着天花板上缓缓旋转的环形音箱阵列。配文只有八个字:
**听见他人,照见自己。**
几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来函件,提名“中国声音档案馆”参评年度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审意见写道:“该项目以极简的技术手段,实现了最深刻的人文关怀,展现了21世纪最具温度的文化实践。”
而此时的林浩然,已踏上前往云南边境的旅途。那里有一群傈僳族老人,正等着他帮他们录制濒危语言的口传史诗。据说,会讲这种方言的人,全世界不足三十。
越野车行驶在蜿蜒山路上,收音机里恰好播放着《风经过我的名字》。童声清澈,穿透层叠云雾。
他摇下车窗,任山风吹乱白发。
他知道,这场关于倾听的长征,远未结束。
只要还有人在说话,他就不会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