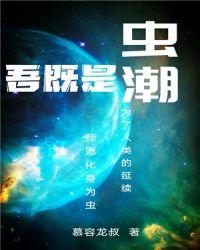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62章 哪一张是高贵的哪一张是龌龊的(第2页)
第662章 哪一张是高贵的哪一张是龌龊的(第2页)
>我们谁都没说话,只默默重来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满意为止。
>回程路上,我把那段录音放给司机听。他是傈僳族,不懂独龙语,听完却红了眼眶。他说:‘这声音像雪山上的风,吹了几千年,不该在我这一代断掉。’”
林浩然读完,闭上眼,久久未动。
飞机起飞时,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舷窗上。他戴上降噪耳机,播放了一段私人收藏??那是他父亲生前最后一次通话录音。老人躺在病床上,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断续地说:“浩然啊……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念《岳阳楼记》吗?‘先天下之忧而忧……’你现在做的事,比当明星有意义多了。”
那是三年前的事。一个月后,父亲走了。
林浩然一直没敢删这段录音。每次怀疑自己是否走得太远、太偏、太孤独时,他就听一次。
他知道,这条路注定不会热闹。聚光灯下的掌声终会散去,热搜榜单每日刷新,唯有那些藏在山野深处、炕头灶边、坟前碑后的低语,才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心跳。
抵达西昌后,他转乘大巴,再换越野车,历经十个小时颠簸才进入大凉山腹地。迎接他的是当地文化站站长吉克,一位四十多岁的彝族汉子,皮肤黝黑,眼神锐利。
“林老师,毕摩阿沙老爷等您三天了。”吉克一边开车一边说,“他原本不肯见外人,但听说您是从云南怒夺村来的,就说:‘那是听天语的人,可以相见。’”
当晚,他们在一座半山腰的木屋住下。夜里风雨骤起,雷声滚滚,仿佛群山在低语。林浩然躺在床上,听着屋顶噼啪作响的雨声,忽然想起阿芮婆唱《七夜》最后一段时的情景??也是这样的夜晚,也是这样的风雨,也是那样一句句从生命尽头挤出来的歌声。
第二天清晨,他们徒步两小时登上一处陡峭台地。那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石庙,门前挂着牛骨与铜铃,空气中弥漫着柏枝燃烧的气息。毕摩阿沙早已等候多时。他年逾九十,背驼如弓,双眼浑浊,却仍戴着象征身份的鹰羽冠和漆皮法帽。
见面无言。林浩然依习俗跪下行礼,敬酒,磕头。老人伸出枯瘦的手,轻轻扶起他,然后缓缓坐定,取出一面羊皮鼓。
鼓声响起,低沉悠远,如同大地脉搏。
紧接着,他开始吟诵《指路经》的第一章??《灵魂启程》。声音苍老却不颤抖,每一个音节都像刻在岩石上的符文,带着神秘的韵律与力量。林浩然屏息凝神,将双声道麦克风置于最佳角度,同时启动三台备用录音设备。
随着经文推进,内容逐渐深入:亡魂需穿越九重山脉、七条毒河、一片迷雾森林,最终抵达祖先居住的“兹兹蒲武”。途中每遇险境,皆由毕摩以特定咒语为其开道。而这些咒语,使用的是古彝语中最隐秘的“祭语法”,现代彝语使用者几乎无人能解。
整整四个小时,老人未曾停歇。期间只饮了一小口蜂蜜水,便继续吟唱。林浩然几次想劝他休息,却被吉克悄悄摇头制止:“这是神圣仪式,中断即失效。”
直至夕阳西下,最后一句经文落下,老人缓缓放下鼓槌,整个人似被抽空力气,靠在石柱上微微喘息。
林浩然含泪上前,深深鞠躬:“谢谢您,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
老人睁开眼,竟露出一丝笑意:“你不只是来录音的,你是来接引的。我昨夜梦见祖先说了:‘声音回来了。’”
那一刻,林浩然忽然明白??他们所做的,从来不是“抢救”什么,而是参与一场跨越生死的交接仪式。每一个愿意开口的老人,都是在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托付给未知的未来。
返回途中,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今天我们总说‘传承文化’,好像那是一件可以打包交付的工作。
>可真正的传承,是信任。
>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愿意把他族群最核心的秘密,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人听。
>他不怕被盗用,不怕被误解,只怕没人听得懂。
>所以他唱,哪怕耗尽最后一口气。
>而我们所能做的,唯有跪下,接过这份沉重的馈赠,并承诺:
>它不会在我手中熄灭。”
一周后,林浩然回到北京。还未进办公室,就被周阳拦住:“出事了!”
原来,某境外NGO突然发布声明,指控“语言方舟行动”涉嫌非法采集少数民族语音数据,企图“构建民族意识数据库”,并附上了几张模糊的照片??正是他们在怒夺村工作的场景。
舆论瞬间发酵。一些自媒体趁机炒作,称林浩然是“文化间谍”,目的为分裂国家。社交平台出现大量攻击性言论,甚至有人扒出他早年出演电视剧《洪世贤传奇》时的角色黑历史,恶意关联“伪君子”“表里不一”等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