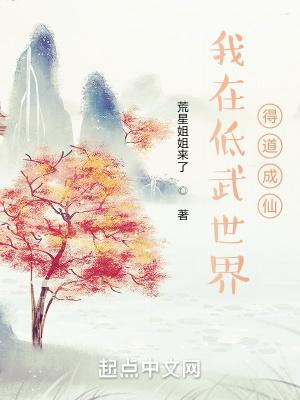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63章 祁厅长你高攀了(第1页)
第663章 祁厅长你高攀了(第1页)
不容易啊,可算回来了,这都十多二十天了。
再耽搁下去,自己的这戏就真的很难拍了……李陆万分感慨。
“大厅……长?”祁讳脸有点黑,大厅长是什么奇葩称呼?大堂经理吗?
随着李陆一声惊呼,。。。
夜雨落在北京城外的山脊上,像无数细小的手指敲打着大地。林浩然站在中华世纪坛展览馆后门的台阶上,任雨水顺着伞沿滑落。闭展已三个小时,工作人员早已离去,只有清洁工在远处收拾残余的展板。他没有走,仿佛还听见那些声音在耳边回响??怒夺村的傈僳语、凉山的古彝音、独龙江畔断续的婚嫁歌……它们交织成一片看不见的网,将他的灵魂牢牢缠住。
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周阳发来的照片:云南独龙江乡的小木屋前,莉娜玛奶奶坐在藤椅里,手里捧着一台“声音种子盒”,正笑眯眯地听着自己唱过的那首婚嫁歌。她身边站着两个小女孩,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嘴里跟着哼哼唧唧地模仿。配文只有一句:“她说,今天梦里不安静了,全是歌声。”
林浩然笑了,眼眶却湿了。
他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然复活。不是靠政策文件,不是靠学术报告,而是靠着一句句被重新拾起的话语,在孩子唇齿间笨拙而真诚地流转。就像春天的第一缕风,吹过冻土,未必立刻催生绿意,但大地已经感知到了温度。
他收起伞,走进雨中。雨水打湿了他的外套和头发,但他不在乎。这一刻,他不想躲进任何庇护所。他想让身体也记住这场雨,记住这个属于“听见”的夜晚。
回到档案馆已是凌晨。地下三层的灯依旧亮着,像一座沉入海底却不肯熄灭的灯塔。他脱下湿衣,换上干爽的毛衣,打开电脑,调出最新一批采集数据。四川凉山毕摩阿沙老爷吟诵的《指路经》已完成初步转录,共十二章,总计五万三千余字,全部使用古彝语书写系统标注,并附有语音波形比对图谱。语言学家团队评价:“这是近三十年来最完整、最权威的《指路经》版本,极可能成为未来彝族文化研究的基准文本。”
可林浩然知道,真正的价值不在学术圈的认可,而在那一日老人放下鼓槌时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来录音的,你是来接引的。”
他点开音频文件,播放最后一段??《归途之门》。老人的声音已近乎呢喃,却依旧坚定:
>“越过黑水河,踏碎迷雾石,
>祖先之地兹兹蒲武,在星落之处等你。
>若有人为你传声,莫惧前行;
>若无人应答,魂亦自归。”
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从时间深处凿出来的碑文。林浩然闭上眼,任其灌入耳中,流遍全身。他忽然意识到,这些经文不只是为亡者指引方向,更是为生者划定边界: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留在这个世界?
第二天清晨,赵明远推门进来时,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脸贴在键盘上,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桌上摊开着笔记本,一页纸上写着几行潦草的字:
>“当一种语言消失,不只是词汇死了,
>是整个世界的某种颜色褪去了。
>我们以为还能用别的话讲述它,
>可其实,那片色彩再也无法被看见。”
赵明远轻轻叹了口气,把外套披在他肩上。
“你非得把自己熬干才甘心?”他低声说。
林浩然惊醒过来,揉了揉眼睛:“没事儿,就是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
“梦见我在一条河边上走,河水漆黑,上面漂着许多纸船,每一只都写着一种语言的名字。有的已经沉了,有的还在飘。突然有个小孩跑过来,往河里放了一只新的船,上面写着‘傈僳语?怒夺村方言’。他还冲我挥手,说是林老师教他的。”
赵明远沉默片刻,坐下来:“你知道吗?教育部昨天开会,讨论要不要把‘语言方舟’纳入国家非遗数字化工程试点项目。”
林浩然一愣:“真的?”
“真的。”赵明远点头,“而且有几个省已经开始主动联系咱们,想建立地方协作站。贵州雷公山那边甚至提出,愿意让苗族青年志愿者免费培训两年,专门做母语记录。”
林浩然怔住了。三年前,他们申请一辆越野车进村都要层层审批;如今,竟有人主动伸出援手。
“变天了。”他说。
“不是变天,是你坚持得太久。”赵明远看着他,“人们终于看懂了你在做什么??不是保存死语言,是在唤醒活记忆。”
中午,林浩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新疆伊犁。
“林老师……我是巴特尔的孙女,叫其其格。”女孩声音轻柔,带着明显的蒙古语口音,“爷爷留下的磁带,您修复好了吗?”
林浩然心头猛地一颤:“你……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附件里看到您的名字。我试了好多次邮箱都没回信,只好打电话……对不起,打扰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