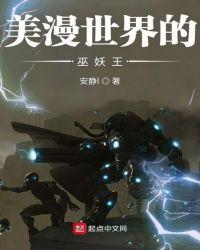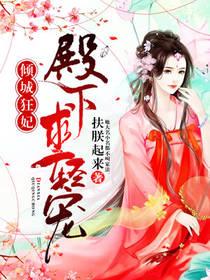笔趣阁>得罪资本后,我的歌越唱越红 > 第二百九十七章 消费爱国情怀牟利免费无限期授权了解一下(第3页)
第二百九十七章 消费爱国情怀牟利免费无限期授权了解一下(第3页)
而此时,沈铭恩已踏上新的旅程。
在贵州黔东南,一位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邀请他录制濒临失传的“蝉歌”??一种模拟昆虫鸣叫的复调合唱技法;在新疆喀什,一位维吾尔族木卡姆艺人希望他帮忙保存一套完整的十二木卡姆演奏实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三位年逾八旬的长调牧人联名请求:“让我们把《骏马赞》唱完吧,趁还能喘气。”
他随身携带的十台录音笔,如今已全部投入使用。每到一处,他不再只是记录者,而是参与者、学习者、传递者。他学会了用苗银刀划破指尖向祖灵起誓,学会了在瑶山清晨面向东方默诵经文,学会了在草原上仰卧倾听风吹过马头琴弦的震颤。
他曾以为自己是在对抗遗忘。
后来才明白,他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为一首歌耗尽最后一口气,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失去它。
某夜宿于湘西土家族村寨,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我曾以为文明会死于战火,
后来发现它更常死于沉默。
没有人唱,没有人听,没有人记得。
然后某一天,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
用尽最后力气哼出一句童谣,
你就知道??
火种从未熄灭,
只是藏在灰烬之下,
等人弯腰,轻轻吹一口。**
**而我所做的,
不过是俯身的姿态足够低,
耳朵足够诚,
心足够疼。”**
窗外,月光洒在吊脚楼上,远处传来隐约的山歌。
他轻轻拿起骨笛,吹响阿?教他的那段飞歌旋律。
笛声悠远,穿林渡水,像是回应,又像是召唤。
他知道,这条路没有终点。
但他也知道,
只要他还走得动,
就会一直走下去。
因为总有人,在黑暗中等着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