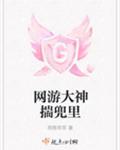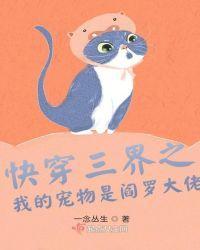笔趣阁>得罪资本后,我的歌越唱越红 > 第二百九十七章 消费爱国情怀牟利免费无限期授权了解一下(第2页)
第二百九十七章 消费爱国情怀牟利免费无限期授权了解一下(第2页)
“我可以复述一遍吗?”沈铭恩问。
老人点头。
沈铭恩清了清嗓子,努力模仿那独特的腔调与节奏,一字一句地重复。起初生涩拗口,几次卡壳,但在老人细微的手势提示下,渐渐找到了那种绵延不绝的气息流动感。
当他完整念完最后一句,老人睁开了眼,眼中竟闪过一丝泪光。
“你记住了。”他说,“不只是耳朵听见了,心也接住了。”
当晚,全村举行了一场小型仪式。村民们聚集在废墟般的盘王庙前,点燃篝火,摆放祭品:糯米酒、腊肉、野果、新采的艾草。七位年长者围坐一圈,手持?具,为此次传音祈福。
沈铭恩被请至中央,面前放着一面小羊皮鼓。老人由孙子扶着坐起,将一根红绳系在他右手腕上,另一端缠绕在自己枯瘦的手指间。
“从今往后,你就是《盘王大歌》的见证者。”老人说,“若我今日死去,你要替我完成剩下的十一卷。哪怕没人听,你也得唱。”
沈铭恩低头,泪水滴落在鼓面上。
“我答应您。”他说,“哪怕走遍天涯,我也要把这首歌带回人间。”
老人笑了,那是沈铭恩见过最安宁的笑容。
仪式结束后,他回到借宿的木屋,打开电脑回放录音。频谱分析显示,那段吟诵的基频极低,约在65Hz左右,接近人类语音极限,且含有大量非谐波成分,类似喉音唱法中的“双声”技巧。更惊人的是,整段音频中存在一种规律性的次声波脉冲,频率恰好与心跳同步??仿佛这首歌本就是为生命节律而生。
他忽然明白为何现代录音设备难以完整捕捉这类古老歌谣。它们不是为了传播设计的,而是为了“共振”??与天地共振,与祖先共振,与听者的血脉共振。
第二天清晨,老人执意要再唱一遍《开天辟地歌》,这次由沈铭恩伴奏击鼓。鼓点按照特定节奏敲击,每三拍一次重击,象征盘王踏步开山。老人的声音依旧虚弱,但在鼓声引导下,竟奇迹般稳定下来,甚至透出几分庄严。
唱至高潮处,他忽然睁开双眼,目光如炬,直视东方初升的太阳。
“天地有灵!”他高喊一声,随即喷出一口鲜血,染红胸前衣襟。
众人惊呼欲上前,却被他抬手止住。
“别怕。”他笑,“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光了。但我知道,歌还在。”
说完,他缓缓躺下,呼吸渐弱。
三个小时后,盘九龄去世。
全村哀恸。按照瑶族习俗,遗体停放三日,期间由亲属轮流守灵并吟唱《盘王大歌》片段。沈铭恩主动请求参与守夜,并承诺每日吟诵第一节,直至葬礼结束。
第三夜,暴雨倾盆。闪电划破夜空,雷声滚滚如战鼓。就在午夜时分,沈铭恩正低声吟唱,忽然发现窗外站着十几个村民,全都披着蓑衣,手持火把,静静地听着。
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原本已不再会唱任何一段《盘王大歌》,但在过去三天里,他们悄悄翻出了祖辈留下的零星笔记,拼凑记忆,重新学习。此刻,他们站在雨中,跟着沈铭恩的节奏,轻声附和。
那一晚,歌声穿透风雨,在山谷间回荡。
葬礼当天,沈铭恩将录制的《开天辟地歌》播放给全体村民听。当老人那虚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时,许多人跪地痛哭。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颤巍巍走上前,掏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递给沈铭恩。
“这是我父亲写的,几十年不敢拿出来。”她哽咽道,“现在,我想让它见光。”
沈铭恩接过本子,翻开第一页,只见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录着《盘王大歌》第二卷《迁徙之路》的部分歌词。虽然残缺不全,却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当场宣布:“我会把这段录音和手稿上传至‘声命’平台,并发起‘瑶音重生计划’??招募志愿者前往各地寻找幸存传人,系统性整理、录制、翻译所有现存版本的《盘王大歌》。”
消息发布后二十四小时内,平台收到超过两千条响应。广西、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区陆续有瑶族村落联系“声命”,表示愿意开放家族秘传歌本。更有数十位民族学者主动请缨加入项目组。
一个月后,国家非遗中心正式立项支持该项目,并拨款建立“瑶族口头传统数字档案库”。那位曾质疑沈铭恩“情绪消费传统文化”的权威专家,在看过《开天辟地歌》录音频谱与现场视频后,公开发表道歉信:“我们长期迷信文本与物质遗产,却忽视了活态传承中最核心的部分??声音本身所承载的生命能量。沈先生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