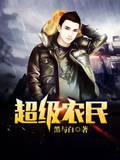笔趣阁>塌房?我拆了你这破娱乐圈 > 第518章 世界第三实时胜率15(第2页)
第518章 世界第三实时胜率15(第2页)
周南沉默了很久。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阳台栏杆上,叽喳两声,又扑棱飞走。
“如果拍,就不能只拍我。”他终于开口,“要拍李静和她丈夫抱着牌子站在樱花树下的样子;要拍听障舞者用手语演绎《我还在这里》时颤抖的指尖;要拍青海盲童们摸着溪水石头哼出旋律的模样。还有……我女儿第一次走路那天,在油菜花田里喊‘看我跑啦’的那一瞬。”
“你能接受镜头直面这些?”林晚问。
“我不是为了被看见才做这些事。”他说,“但如果有人因此开始倾听,那就不该拒绝被看见。”
电话挂断后,他起身走到客厅,发现女儿已经醒了,正扶着沙发边缘试图站起来。肖萌蹲在她面前,鼓励地拍着手。
“加油!再往前一步!”
小女孩摇晃了一下,迈出左脚,右脚跟上,踉跄几步,扑进了妈妈怀里。
周南掏出手机,录下了这一幕。没有滤镜,没有配乐,只有真实的喘息、笑声和一句含糊却清晰的“妈妈抱”。
他把视频上传到“声音种子计划”的私密群组,附言:“今天,我们又赢了一次。”
群里很快回复不断。
广州那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儿子留言:“我爸今天突然叫我‘小军’,那是他年轻时给我起的乳名,三十年没人这么叫过了。我放了你们上次分享的铁路建设工地录音,他听了很久,眼角有泪。”
周南回了个拥抱表情。
晚上,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再次打开《未完成的告别》的工程文件。技术人员建议加入一点环境混响,让那段微弱的呼吸声更“可听”。但他删掉了所有后期处理层,只保留原始波形。
“它不需要被美化。”他在日记里写道,“它需要被尊重。”
夜深人静时,他梦见了小宇。男孩坐在一片星空下,身边漂浮着无数细小的光点,每一个都对应一段声音:吞咽的“咕”声、呼吸的节奏、那半秒模糊的“啊”。小宇抬头看他,笑着说:“周南叔叔,我现在会唱歌了。”
醒来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
第二天一早,他们如约前往女儿所在的特殊教育资源学校。新装的“录音角”已完成布置:一面墙上挂着三十个彩色声音胶囊,每个里面储存着孩子们录制的日常片段??咳嗽声、拍手声、哼唱跑调的儿歌、甚至一次成功的“老师早上好”。
校长亲自迎接他们,带着一群教师和学生来到小广场。孩子们围坐一圈,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戴着助听器,有的眼神迟缓却专注。当周南拿出便携录音机播放《奔跑的春天》时,全场安静下来。
音乐结束,一个小女孩举起手,用手语比划:“我想录一句话送给妈妈。”
老师帮她翻译:“她说,‘妈妈,我爱你,虽然我说不出来,但我心里每天都在说。’”
周南当场蹲下,帮她按下录音键。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众声》从来不是他的作品,而是千万个被忽视的生命共同写就的诗集。
活动结束后,他和肖萌牵着女儿走在校园林荫道上。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女儿忽然停下脚步,仰头望着天空,指着飞过的鸽群,又一次大声说:“鸟鸟飞高高!”
这一次,她连说了三遍。
肖萌蹲下来抱住她,泪水滑落。
周南没有掏手机,也没有录音。他只是静静站着,把这一刻刻进心里。
回到车上,他打开备忘录,写下一段话:
>真正的记录,不只是保存声音,更是守护每一次发声的勇气。
>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机会说出“我在”,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
>即使声音微弱如尘,也值得被世界认真倾听。
三天后,“声音种子计划”官网悄然上线一个新功能:“回声信箱”。用户可上传一段亲人留下的声音,系统将生成一封虚拟信件,以AI模拟语气朗读出来,供家属收听。第一封信来自李静。她上传了小宇最后一次成功眨眼时监护仪发出的“嘀”声,系统将其转化为一句话:
“妈妈,我没有害怕。我只是累了,先睡一会儿。”
她在后台留言:“这是我收到过最温柔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