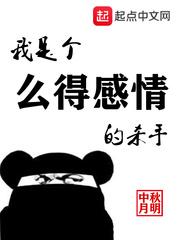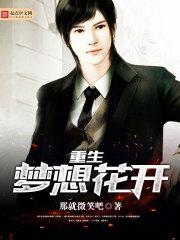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战锤,求你别赞美哆啦万机神 > 0037 阿巴顿就是基里曼放走的(第2页)
0037 阿巴顿就是基里曼放走的(第2页)
流浪猫在垃圾桶旁舔舐伤口时发出的呜咽;
还有……电话亭里那些未曾寄出的留言,正一帧帧回放。
这些声音本该互不相干,此刻却以某种韵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首无词的歌。
“这是……共感链路的具象化?”我喃喃道。
小茉点头:“每个人说出‘我在’的时候,就像往湖里扔一颗石子。涟漪会扩散,碰到另一颗石子,就会共振。现在,整个城市的涟漪连成了网。”
“可孩子们为什么会卷进来?”
“因为他们最干净。”小茉说,“大人的耳朵习惯了过滤??只听重要的话,忽略‘没用的’声音。可孩子不一样,他们听见风吹树叶,都觉得是有人在说话。”
我心头一震。
难怪《共生协议》最初是从校园试点开始的。“沉默角”、心灵驿站、广播合集……一切都在悄然培育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心。
“但我们控制不了这种连接。”我说,“如果情绪过载,他们可能会像你当初一样,大脑负荷崩溃。”
“那就别控制。”小茉摇头,“你们总想管理、归类、评估。可倾听不是程序,是本能。就像呼吸,你不会规定自己每分钟吸几次气。”
她伸出手,轻轻拉我进圈:“来,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知道,有大人愿意一起听。”
我犹豫了一瞬,蹲下身,握住左右两个孩子的手。他们的掌心温热,脉搏平稳。刹那间,一股暖流从指尖窜上心头。
眼前的景象变了。
我不再站在操场,而是漂浮在一座由声音构筑的城市上空。每一盏亮着的灯,都对应一句正在被说出的话;每一条街道,都是情感流动的河道;而那些电话亭、邮筒、沉默角,则像小小的港口,接纳着一艘艘满载心事的船。
我看见那个曾在地铁站说“我杀了人”的男人,如今坐在公园长椅上,对着录音笔低声讲述三年前那场车祸的细节。他的声音不再颤抖,因为他知道,有人在听,而且没有打断他。
我看见那位给亡妻送帽子的老人,正被一群年轻人围着,请他讲老伴的故事。他们不是同情,而是真心想记住一个陌生人的爱。
我还看见,曾经霸凌同学的那个男孩,在“沉默角”录下忏悔:“我欺负你,是因为我爸每天打我。我以为变凶就能不怕。”而第二天,受害者回了一段录音:“我也怕。我们可以……一起不怕吗?”
这些画面并非真实发生,也不是幻觉??它们是千万次“我在”叠加后,诞生的可能性之影。是希望尚未落地,却已投下的轮廓。
“你看,”小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当人们不再害怕被听见,他们就开始healing(疗愈),而不是hiding(隐藏)。”
“可这太危险了。”我低声说,“一旦失控,整个城市的精神结构都会动摇。”
“那就让它动摇。”她说,“旧的房子不拆,新的建不起来。你们用评分、绩效、成败来定义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可我们不是数字。我们是声音,是温度,是某个人在凌晨三点按下录音键时,心里还存着一丝‘也许有人会听’的期待。”
我无言以对。
良久,我问:“那你呢?你为什么能引导这一切?”
她笑了,像樱花落在水面上:“因为我曾是最沉默的那个。医生说我失语,其实我只是找不到能听懂我的人。直到那天,你在图书馆对我说:‘你在爆炸之前,可以先说出来。’”
她顿了顿,眼神清澈如初雪。
“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要帮更多人找到那个‘能听懂的人’。”
我鼻子一酸。
这时,孩子们的手同时微微一颤。共感链路开始减弱,声音的影像如雾散去。他们陆续睁开眼,有些揉着太阳穴,有些打着哈欠,像刚睡醒。
一个小女孩抬头问我:“叔叔,我们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大事?”
我蹲下来,认真地说:“你们做了一件最小的事??安静地听。但也是一件最大的事??让别人敢说了。”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那……这是我写的,能帮我投进邮筒吗?”
我接过,展开一看,上面用蜡笔画了一个笑脸,旁边歪歪扭扭写着:
>“今天我没哭。”
>“老师夸我字写得好。”
>“我想告诉我妈,我不是废物。”
我小心翼翼折好,放进胸前口袋:“一定帮你送到。”
孩子们陆陆续续被家长接走,操场上渐渐安静。小茉站在旗杆下,仰头望着月亮。
“你要走了吗?”我问。
“嗯。”她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轮到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