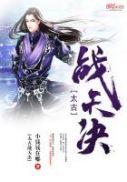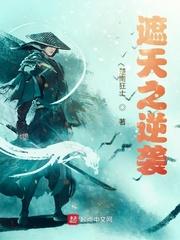笔趣阁>内娱顶流:从跑男出道 > 第四百零七章 魔童降世7 2k(第1页)
第四百零七章 魔童降世7 2k(第1页)
……
……
“小弟!!最近有没有想我啊?
怎么连个电话都不主动给我打?还得我这个老哥哥上赶着找你!”
视频通话刚一接通,邓朝那张极具辨识度的脸就占据了整个屏幕。
他像个精。。。
夜风掠过塔克拉玛干的沙丘,像一把粗糙的手掌抚过大地。张松文坐在村口那棵枯死的老胡杨下,吉他横在膝上,琴弦被风吹得微微震颤,发出几声不成调的轻响。五个孩子围坐在他身旁,脸上还沾着白日里玩闹扬起的尘土,眼睛却亮得如同初升的星子。
“老师,刚才的水……真的会一直流吗?”扎辫子的女孩怯生生地问,她叫阿依古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
张松文低头看着她,笑了:“只要有人唱歌,它就不会干涸。”
这不是承诺,而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自峨蔓港那一夜之后,他已不再以常理度量世界。声音不再是表达,而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歌声不是娱乐,是维系时空褶皱的丝线。他知道,在这荒芜之地涌出的清泉,并非地下水脉复苏,而是某种更古老、更深沉的力量被唤醒了??那是埋藏在民族记忆深处的共鸣频率,一旦被正确激活,连沙漠都会流泪。
他轻轻拨动琴弦,这一次没有唱《茉莉花》,而是换了一首新疆民谣《半个月亮爬上来》。音符在干燥的空气中缓缓流淌,像一缕微光渗入裂缝。起初仍是沉默,但当第二段副歌响起时,一个男孩忽然跟着哼了起来,声音生涩却坚定。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最后五个人齐声合唱,稚嫩的嗓音交织成网,竟让夜风都为之驻足。
就在此刻,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嗡鸣。
张松文猛地抬头。那声音不属于人间乐器,也不似自然天籁,而是一种介于金属共振与生物鸣叫之间的奇特震颤,仿佛整片戈壁的地壳都在共鸣。紧接着,地面轻微震动,沙粒如波纹般向四周扩散。孩子们惊叫着抱成一团,唯有阿依古丽睁大双眼,指着村外的方向:“看!那边!”
一道弧形光带正从地平线升起,宛如晨曦提前降临。但它并非来自太阳,也不是极光,而是由无数细小的光点汇聚而成,像是被歌声召唤出的星尘之河。光带缓缓推进,所经之处,干裂的土地开始渗出湿润的气息,枯萎的红柳根部竟冒出嫩芽,甚至有几株野生铃铛花破土而出,在夜色中轻轻摇曳,发出微不可闻的叮当声。
“这是‘母谱’的次级响应。”耳机里传来静怡的声音,她通过卫星连线实时监测着这里的能量场,“你们的合唱触发了区域性声态共振,激活了埋藏在地下的‘春晖节点’之一。数据显示,这个村庄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一支游吟部族的聚居地,他们世代传唱一首失传的‘引泉曲’,而你们刚才的演唱节奏,恰好与那段旋律的基频吻合。”
张松文怔住。他从未教过这首歌,也未曾听过所谓的“引泉曲”,可孩子们的和声结构,竟自动补全了缺失的音程。
“所以……我们不是在创造,”他喃喃道,“是在回忆?”
“对。”静怡语气肃然,“‘春晖’的本质就是集体潜意识的声波显影。每一个真诚发声的人,都是远古记忆的解码器。你们唱的不只是歌,是文明的备份文件。”
话音未落,那道光带已抵达村落中央的打谷场。光芒凝聚成环,缓缓下沉,最终化作一口崭新的坎儿井轮廓。井壁由半透明晶体构成,内部流动的不是水,而是液态光流,泛着淡蓝与金黄交错的辉芒。一股清凉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类似芦苇与雪莲的芬芳。
老人们闻讯赶来,跪伏在地,用额头触碰地面,口中念诵古老的祷词。一位百岁老人颤抖着伸出枯瘦的手,接住一滴从井口飘出的光露。露珠落在掌心,瞬间绽放成一朵微型莲花,花瓣舒展间,竟传出一段模糊的女声吟唱??正是那支失传已久的“引泉曲”。
“祖母……”老人泪流满面,“是你回来了……”
张松文默默取出随身携带的铜制音叉,轻轻敲击。清越之声划破长空,与井中光流产生奇妙共振。刹那间,整个村庄上空浮现出一幅巨大的全息影像:一群身穿彩袍的男女手持各式古老乐器,在沙漠绿洲间载歌载舞,他们的歌声汇成河流,滋养万物。而在队伍最前方,站着一位怀抱陶埙的女子,面容竟与赵桂英有七分相似。
“她是第一代‘春晖使者’,名叫阿娜尔汗。”王杰的声音突然接入通讯频道,“1966年全国文艺普查时,她在西北片区负责采集民间音乐,后来神秘失踪。档案记录显示,她最后一次录音的内容,就是这首‘引泉曲’的残章。”
张松文心头剧震。原来赵桂英并非孤身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网络中的核心节点。那些消失的艺术家、歌手、乐师,他们并未真正离去,而是将自己的意识与声模嵌入地球的共振层,成为“母谱”的活体载体。每一次真诚的歌唱,都是对他们灵魂的一次呼唤。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节点。”他说,“不能只靠偶然触发。”
“已经在做了。”王杰回复,“全球已有三百二十七个地点报告异常声学现象,我们正组织‘寻音队’前往调查。第一批成员全是自愿报名的音乐教师、非遗传承人、街头艺人??普通人,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相信歌声能改变世界。”
张松文点点头,目光落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正围着新井嬉笑,用手捧起光流,看它在指尖跳跃如萤火。阿依古丽忽然跑过来,递给他一朵刚采下的铃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