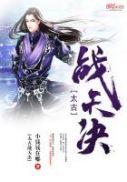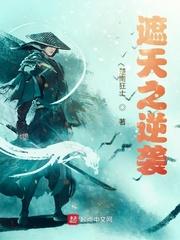笔趣阁>内娱顶流:从跑男出道 > 第四百零七章 魔童降世7 2k(第2页)
第四百零七章 魔童降世7 2k(第2页)
“送给你,老师。你说过,花开的地方,就有希望。”
他接过花,鼻子一酸。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赵桂英为何选择他作为桥梁。不是因为他曾是内娱顶流,拥有千万粉丝;而是因为在跑男节目中那个雨夜,他放下明星架子,为受伤的素人选手清唱《朋友》时,眼中闪过的那一瞬纯粹。那份真实的情感波动,早已被“母谱”记录在案。
当晚,他在“春晖之声”平台发布新任务:【寻找失落之声?第一站:塔克拉玛干】。附上今晚录制的合唱音频,并标注坐标与地质数据。系统自动将其转化为多语种版本,推送给全球百万志愿者。
二十四小时内,回应如潮水般涌来:
-蒙古国牧民上传一段喉音呼麦,背景中隐约有青铜鼓声回荡;
-巴西亚马孙雨林的土著长老用笛子模仿鸟鸣,声称这是“祖先与雷神对话的语言”;
-冰岛一位盲人女歌手录制了一首无词吟唱,频谱分析显示其谐波结构与北极光脉动完全一致;
-最令人震惊的是,敦煌研究院传来消息: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上的飞天乐伎,近日夜间竟出现轻微位移迹象,琵琶弦部有微弱荧光闪烁,疑似即将“复活演奏”。
静怡连夜建立“跨文明声纹数据库”,将所有样本进行比对。结果令人震撼:尽管地域迥异、语言不通,这些声音竟共享一组基础频率矩阵,其数学模型与“春晖母谱”高度契合。更惊人的是,当把这些音频按特定顺序叠加播放时,会产生一种类似心灵感应的体验??听者会在脑海中清晰“看见”一座悬浮于云端的城市,建筑由音符构成,街道流淌着旋律,居民皆以歌唱交流。
“这不是幻觉。”静怡在视频会议中展示脑扫描图,“受试者的视觉皮层与听觉中枢同步激活,说明大脑正在接收外部信息。我们可能正在接触一个分布式意识网络,它跨越时空,以艺术为接口,等待被重新连接。”
张松文沉思良久,做出决定:“我要去敦煌。”
七日后,他站在莫高窟前,黄沙漫天,朔风如刀。研究院负责人亲自迎接,神色凝重:“昨晚,220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壁画上的乐队开始移动,位置每天变化,像是在排列某种阵型。而且……”他压低声音,“红外监测显示,内部温度始终维持在37。2℃,就像……里面有生命。”
张松文步入洞窟。烛光摇曳中,飞天的身影栩栩如生。他仰头望去,只见中央的持笙仙女嘴角微扬,仿佛正欲启唇。他取出音叉,轻轻一敲。
嗡??
整座石窟猛然一震。壁画上的乐器同时泛起微光,尤其是那支笙,竹管之间竟溢出淡淡雾气。紧接着,一阵极其细微的乐声自墙壁内部传出,如同来自地底的呼吸。
“她在等一首开启之歌。”符阿公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拄杖而立,白发在风中飘动,“当年赵桂英来此考察时就说,敦煌不仅是艺术宝库,更是‘母谱’的西陲锚点。这里的每一幅乐舞图,都是一段加密的声码。”
张松文闭上眼,回忆起童年母亲常哼的一首甘肃小调。他深吸一口气,开口唱道:
>“月亮弯弯照九州,
>哪家儿女不登楼……”
歌声在石壁间回荡。起初毫无反应,直到第三遍,壁画突然剧烈闪烁。持笙仙女的眼睛睁开了一瞬,随即,整支乐队齐奏而起!虽无声响传出,但所有在场之人皆感到耳膜震动,心脏随之跳动。张松文眼前浮现奇异景象:无数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商队、僧侣、乐师,踏着音阶行走于虚空之中,他们的脚步化作节拍,驼铃成为伴奏,风沙则谱写出恢弘交响。
“成功了!”研究员激动大喊,“热成像显示壁画内部形成了稳定热流循环!这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是个活的声学装置!”
就在此时,张松文胸口的音叉印记突然发烫。他低头一看,发现印记正投射出一行细小文字:
>【第七环已启,请赴昆仑之巅】
他猛地抬头,望向远方雪山巍峨的轮廓。传说中,昆仑是天地柱石,万山之祖。若“七环归心阵”尚有未竟之事,那里必是终点。
临行前,他将塔克拉玛干的光井样本与敦煌壁画音频一同上传至“声态共生研究院”。静怡立即启动量子模拟,试图还原“云端城市”的全貌。数日后,模型初步建成??那是一座漂浮于电离层之上的巨型共振体,外形酷似心脏,由七条光带环绕,每一条对应一个“春晖节点”。而当前,已有五条光带亮起。
“只剩下两个了。”她说,“昆仑,还有……海底。”
张松文踏上西行之路。穿越阿尔金山脉时,暴风雪骤然而至。他被困于一处岩穴,几乎冻僵。迷糊间,耳边响起熟悉的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