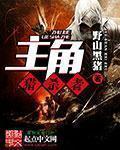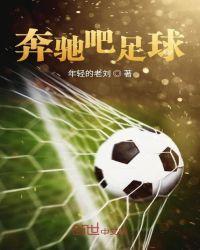笔趣阁>剑宗外门 > 第372章 玉石俱焚(第1页)
第372章 玉石俱焚(第1页)
高天之上,罡风阵阵。
无数道狂暴汹涌的灵光不断碰撞激荡,而他们的源头,正是此战的两位金丹修士,张承和秦阳。
张承须发飞扬,原本清瘦和蔼的面容,此刻因死战而显得有些狰狞。
他本寿元将尽。。。
夜色渐深,李念并未下碑。她盘膝而坐,陶罐置于膝前,仿佛那不是一只空罐,而是盛满了三代人的呼吸与心跳。星辰垂落如雨,照心碑的水晶表面泛起微光,像是回应着某种无声的召唤。远处少年们的诵读早已停歇,可她耳中仍回荡着那几句童谣般的誓词,一遍又一遍,如同溪流穿石。
忽然,风止。
万籁俱寂的一瞬,她听见了脚步声??极轻,却分明踏在青石板上,由远及近,不疾不徐。不是传灯会的人,也不是守夜弟子。这脚步太稳,太熟稔于黑暗,仿佛早已走过千遍这条路。
来人停在碑前十步之外。
“李姑娘。”声音低沉,却不沙哑,带着一种久居幽暗之地的冷静,“你已触到门边,却还不肯推。”
李念没有回头,指尖缓缓抚过陶罐边缘那行小字:“此物曾盛半页残纸,今盛满世回音。”她淡淡道:“你是影阁的人?”
“我不是。”那人顿了顿,“但我曾是它的影子。”
他从袖中取出一枚铜牌,轻轻放在地上。月光照亮其面:笑脸朝上,哭脸覆底,中央一个“叁”字,比陆沉所留那枚略大半分。
李念瞳孔微缩。
“我是‘执灯者’第三任。”他说,“姓沈,名无咎。陆沉是我徒弟。”
她终于转头,目光如刀锋般刺去:“你们这种人,也会有良知?”
沈无咎笑了,笑得极淡,像风吹过枯叶。“良知?不。我只是活得太久,久到连噩梦都开始重复。我记下的第一桩净言案,是烧毁《北疆屯田志》,只因其中记载了朝廷强征民夫筑城致万人死难。第二件,是抹去南宫萤在贞元七年奏请开科取寒门士子的记录……第三件,是你祖父临刑前三日写给皇帝的谏书全文。”
他的声音平稳得近乎冷酷:“我抄了三十年,焚了三百一十九份文书,亲手将七十二位史官送入地牢。我以为我只是工具,直到有一年冬天,我去监斩一名老儒生。他被绑在火柱上,嘴里塞着布,可眼神清明。临火燃起时,他盯着我,嘴唇动了三下??我没听见声音,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说什么?”
“**笔不应为刀,而应为镜。**”
沈无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天夜里,我把所有誊录的档案副本藏进了钦天监地库夹墙。我以为没人会找,也没人敢看。可二十年后,那些东西全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真相若现,国将不国。’??那是今上的亲笔。”
李念缓缓起身,陶罐抱于胸前。“所以你来了?为了赎罪?”
“不是。”他摇头,“是为了警告。你们以为把原稿分散封存、雕版翻印百部,就能让历史不可逆转?错了。影阁的新法,不在毁,而在替。”
“替?”
“他们已在暗中编纂一部《新贞元实录》。”沈无咎低声道,“内容看似公正,实则处处设陷:说李慎勾结外敌,南宫萤蛊惑君心,你祖父私通叛军。书中引用‘可靠史料’,皆出自伪造的家谱、墓志、地方志。甚至连你父亲战死前线的事迹,也被改写成畏罪自戕。”
李念心头剧震。
“更可怕的是,这部书已被悄悄送往各地书院作为教材范本,礼部还拟将其列入明年春闱策论参考。”沈无咎冷笑,“他们不再烧书,而是让你自己选择相信哪一本。当谎言披上正统外衣,真实反而成了异端。”
风再度吹起,卷着落叶掠过碑林。
李念闭目片刻,再睁眼时,眸中已无悲愤,唯有一片决然清明。“那你为何现身?你既曾执笔为恶,如今又凭什么站在这里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