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剑宗外门 > 第372章 玉石俱焚(第2页)
第372章 玉石俱焚(第2页)
沈无咎沉默良久,忽然抬手扯下左袖。手臂之上,布满纵横交错的疤痕,最深处几乎可见白骨。“这是我三十年来,每完成一桩净言案后,用刀刻下的数目。三百一十九道,一道不少。我活着,不是为了求赦,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制度可以吃人,但人也可以撕开制度的喉咙。**”
他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递上前:“这是我私藏的最后一份原始行动名录,记录了现存‘新影’全部据点、联络方式、以及……他们的资助者名单。”
李念接过,指尖微颤。
“看完它之后,烧掉。”沈无咎后退一步,“我不会再出现。这一夜,是我为自己写的最后一段历史。”
话音未落,身影已融于夜色,如同从未存在。
李念立于碑顶,手中册子沉重如铁。她没有立刻翻开,而是仰望星空。北斗七星清晰可辨,斗柄正指南偏东??春已深,夏将至。
翌日清晨,她召集传灯会七使,另召三位民间刻工、两名游方医师、一位戏班班主,共十一人,齐聚无名堂密室。
她将沈无咎所赠名录摊开,逐条解读。令人震惊的是,“新影”不仅渗透礼部、国史馆,竟还控制了三家大型印坊与五座官办书院。更有甚者,名单末尾赫然写着两个名字:**礼部尚书裴文渊、钦天监正周景和**??皆是当今圣上倚重之臣,表面清廉刚正,实则长期主持“正史净化工程”。
“他们要的不是掩盖过去。”李念指着名录上一处标记,“而是重塑未来。一旦《新贞元实录》成为官方定本,十年后,百姓只会记得被篡改的历史。我们的努力,将成为‘谣言’;我们的证物,会被视为‘伪作’。”
众人默然。
片刻后,那位戏班班主开口:“李姑娘,我们唱戏的,最懂怎么讲故事。真事若无人信,不如让它变成人人都能听懂的戏文。”
李念眼睛一亮。
当日午后,她亲自主持会议,拟定“百戏传史”计划:以《贞元实录》为核心,编写一系列地方戏曲、评书话本、皮影剧本,涵盖南北腔调、各地方言。内容不限悲壮,亦有温情??南宫萤雪夜护书、樵夫孙女寻稿途中遇狼群自救、老太监跪忏之夜……皆可入戏。
同时,她命工匠秘密重制四十九块雕版,但在每一页正文下方,加刻一行极细的小字,肉眼难辨,唯有用特制药水涂抹方可显现。那是一句句被删去的原文,或是一段段幸存者的独白。
“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单纯对抗。”她在会上说,“而是让真实,长出无数条腿,走进茶馆、田埂、渡口、学堂。哪怕朝廷禁得了书,也禁不了千万人口中的故事。”
五月末,第一批戏班启程南下。他们打着“巡演劝善”的旗号,携带着伪装成乐谱的手抄本,在市集搭台开唱。一出《照心碑下血犹温》连演七日,场场爆满。剧中那位手持竹帚的老妇人形象深入人心,有人甚至称其为“当代女史迁”。
与此同时,李念亲自修订《补遗录》,新增“执灯者之章”,录入陆沉与沈无咎的供述,并附上她自己的批注:
>“恶未必生于人心,有时生于职位。当一个人只需执行命令而不问对错,黑暗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故我敬此二人,非因其过往,而因其终敢直视深渊,并向世人言说其所见。”
六月初,暴雨连绵。南方传来消息:三座城市同时出现神秘火灾,烧毁的正是存放《新贞元实录》样本的官署书库。调查发现,火源来自内部,且每处现场均留下一枚铜牌??正面笑脸,背面哭脸,编号分别为“肆”、“伍”、“陆”。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天罚,有人说这是义士所为。唯有李念明白:**影阁内部,正在分裂。**
她立即下令加快“百戏传史”进度,并派遣信使联络海外商船,催促寻访“海外遗孤”之事。她在回信中写道:“即便此人不愿归来,也请告知他:他的血脉未曾断绝,他的名字,将在新的史书中重新书写。”
七月流火,暑气蒸腾。某夜,一名年轻女子徒步抵达言城,风尘仆仆,背负竹篓。她自称是东海渔村人氏,祖上确有一位“远走扶桑的叔公”,临终前留下一封密封信函,交代后代:“若中原有变,可交予言城照心碑下之人。”
李念颤抖着手拆开信封。
里面并非家书,而是一幅绢画:画中男子身着东瀛武士服,怀抱一卷汉文典籍,立于海边悬崖,身后朝阳初升。画角题诗两句:
>**“孤舟不惧千浪险,
>一笔犹承万古灯。”**
落款:**李承砚,贞元三十二年夏于萨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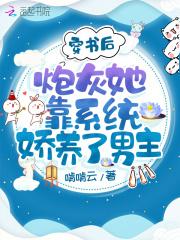
![边疆来了个娇媳妇[年代]](/img/467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