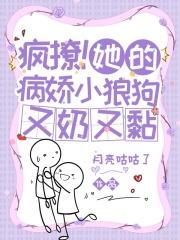笔趣阁>剑宗外门 > 第372章 玉石俱焚(第3页)
第372章 玉石俱焚(第3页)
李念泪如雨下。
她终于确认:李慎之后,真的活着。而且,他教子孙读书识字,代代相传,从未忘记自己的根。
她将此画悬于无名堂正厅,题曰:“承灯图”。并在《补遗录》首页添上一行新标题:
>**《剑宗外门?补遗录卷一:凡人执笔,星火成河》**
秋初,第一场黄叶飘落之时,忆馆迎来一位特殊访客??一名身穿粗麻僧衣的老和尚,自称来自西域大慈恩寺。他带来一幅残破壁画拓片,描绘的竟是当年火烧忆馆那一夜:火焰冲天,书页如蝶飞舞,而在火海之外,七名蒙面人跪地捧书,将文字一口一口吞入腹中。
“这是当年幸存的画僧所作。”老僧合十道,“他们不能带走书,便以身为匣,把整部《实录》默记于心,潜行千里,分别藏于七座寺庙之中。如今,我们愿尽数奉还。”
李念深深叩首。
自此,《贞元实录》不再只是竹简、雕版、戏文,它成了壁画、经咒、僧侣每日诵念的“护法真言”。在高原雪域,在沙漠绿洲,在边陲小镇,都有人在用各自的方式守护这段历史。
冬至前夕,朝廷终于出手。
一道诏书下达:以“淆乱视听、煽动民心”为由,查封全国忆馆,禁止一切非官方史书传播,违者以“妖言惑众”论罪。同时,京畿周边设立十三道关卡,严查往来书籍。
然而,晚了。
《贞元实录》早已化作民谣,在孩童口中传唱;化作药方,在郎中开笺时悄然夹带;化作婚书格式,在乡间新人誓词里嵌入“不忘先贤之痛”八字。
更有甚者,北方某县令在宣读禁令时,竟当众朗读起《悔过席》上老太监的忏悔全文,然后摘下乌纱,长叹一声:“我宁负官职,不负良心。”随即辞职归田。
风波席卷朝野,舆论沸腾。连一向沉默的御史台也有三人联名上奏:“史不可灭,心不可欺,与其堵口,不如开卷。”
十二月初八,雪落无声。李念再次登上照心碑顶,手中握着一封刚刚送达的密信??来自那位商船主:
>“李姑娘:
>我已寻得李承砚之玄孙,名李昭,现为长崎汉学塾教师。彼闻中原往事,泣不成声。虽碍于身份不便归国,然允诺每年清明,率弟子面向东方焚香诵《实录》全文。
>又托我带回一物:乃李慎当年随身玉佩碎片,另一半仍在你处否?”
李念从颈间解下一块残玉,轻轻贴上信纸。
严丝合缝。
她望着漫天飞雪,低声呢喃:“爸爸,爷爷,南宫先生……你们看见了吗?
门,其实一直开着。
我们不是在等待开门的人,我们本身就是那扇门。”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碑林,也覆盖了来路。可在地下深处,七只陶罐静静安放,如同七颗跳动的心脏。
而在无数人家的油灯下,有人正提笔写下这样一句话:
>“今日,我亦为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