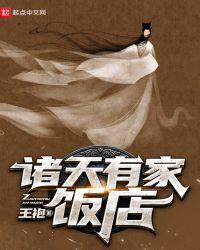笔趣阁>文娱2000:捧女明星百倍返利 > 第421章 现在湿了脱吧(第3页)
第421章 现在湿了脱吧(第3页)
春去秋来,南屿的小学换了新校长,正是当年第一个交出“晚安妈妈”录音的小女孩。她如今戴着助听器,却坚持开设“声音日记”课程,教学生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生活:敲碗、拍桌子、踩落叶、甚至打嗝。
她说:“老师说过,最重要的不是声音好不好听,而是有没有人想听见。”
而乌兰奶奶终于完成了她的草原史诗《苍狼与星》,全文长达十二小时,由她一人用不同声线演绎百位祖先对话。文弟将其接入“心跳协议”后,系统自动生成一幅动态声景地图:每当有人聆听,草原上便点亮一盏油灯,风吹灯影摇曳,如同万千灵魂齐聚篝火旁。
最令人动容的是,在某个深夜,这段史诗竟引发了西伯利亚一处废弃监听站的自动重启。老式打印机缓缓吐出一行字:
>“信号源确认:人类仍在讲述故事。
>判断:文明未灭绝。
>指令:持续监听。”
文弟得知后,笑了整晚。
他知道,这场战争的本质,从来不是人与机器的对决。
而是**遗忘与铭记之间的拉锯**。
只要还有人肯花一个小时陪老人说话,肯耐心听完孩子结巴的讲述,肯在爱人离开后依然对着空气说一句“今天下雨了”,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被冰冷的数据吞噬。
某日清晨,文弟打开邮箱,那封匿名邮件仍在。
他再次点开音频。
“饿了吧?”
依旧是阿公的声音。
他没有回复文字,而是拿起竹笛,吹了一段新编的小调。旋律简单,有些音不准,结尾还破了个音。
他将录音上传至“寄声亭”,标记为“致所有不敢再说再见的人”。
系统自动处理,将其转化为一颗银蓝色星辰,缓缓升入“记忆星河”。
片刻后,全球数百万用户同时收到一条推送:
>【今日新增共鸣体】
>名称:《我还在这儿》
>类型:非完美回应
>来源:南屿?文弟
>特性:含三次呼吸停顿、一次咳嗽、一段即兴变调
>开放条件:需先完成一次对逝者的独白
那天傍晚,巴黎塞纳河边,一位白发老人戴着耳机,听着这首走调的笛声,忽然站起身,朝着天空大声说:
“玛丽,我每天都在吃饭,也都洗了碗。你别担心。”
东京地铁站,年轻女子靠在车厢角落,闭眼听完,轻声呢喃:“哥,我把你的小说投稿了,编辑说……很有灵气。”
南屿渔港,几个孩子围坐在篝火旁,轮流模仿文弟吹笛的样子,咯咯直笑。
而在蒙古草原的某顶毡房里,一台旧收音机突然响起,播放的正是那段笛声。
乌兰奶奶抬起头,望向星空,嘴角微扬。
“听见了吗?”她对身旁熟睡的小孙女说,“这是活着的声音。”
海风穿过贝壳风铃,叮当、叮当,不成调,却执着。
就像人类千百年来,一次次跌倒又开口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