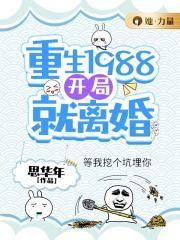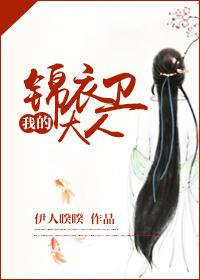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按摩师的自我修养 > 第142章 轻松慢行的发展情况(第2页)
第142章 轻松慢行的发展情况(第2页)
她的声音并不完美,气息仍有瑕疵,但那种穿透灵魂的情感表达,让连最挑剔的老教授都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老教授低声说,“这是命运给过的伤疤,在用歌声说话。”
课后,那个曾经在社交媒体嘲讽她的学生主动找到她,递上一杯奶茶:“对不起,之前我不了解你。能不能……以后旁听你练歌?我也想学会怎么用声音讲故事。”
糖糖接过奶茶,笑了:“可以啊,不过你要请我吃宵夜,练完嗓子我都饿。”
消息传回公司,我们都笑了。但笑完之后,又有些动容??原来真正的反击,从来不是怒吼,而是以实力让敌意闭嘴,让质疑者变成追随者。
与此同时,“重生之夜”的余波仍在扩散。
一家知名公益组织联系到我们,希望联合发起“听见她们的声音”巡回演讲项目,邀请包括糖糖、大鹿在内的多位转型女性讲述自己的经历。第一站定在西南某职业技术学院,那里80%的学生来自农村,许多女孩毕业后被迫进入低端服务业。
出发前夜,我在办公室整理材料,甄仁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剪报。
“你看这个。”她把报纸摊开。
是一篇署名评论文章,标题赫然写着:《当“底层逆袭”不再是个体奇迹,而是系统可能》。
文中提到,过去十年,社会对“草根崛起”的叙事总是聚焦于个别人物的戏剧性转折,仿佛只要足够努力就能翻身。但现实是,大多数人被困在结构性困境中,缺的不是意志力,而是机会和支持系统。
“轻松慢行SPA的‘职业重塑计划’或许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不是制造几个耀眼的榜样,而是构建一条可持续的成长通道。”文章写道,“当企业愿意为员工的未来投资,而不是仅仅榨取其当下价值时,阶层流动才真正有了支点。”
我看完,久久未语。
良久才说:“这篇文章,得放进我们的培训手册里。”
甄仁佳点头:“我已经让团队准备案例汇编了。下一步,我们要把这套模式做成标准化白皮书,免费向社会公开。”
“不怕被人抄?”
“抄得走形式,抄不走初心。”她笑,“而且,如果真能推动整个行业改变,被抄也是一种胜利。”
一周后,巡回演讲正式启动。
首场活动设在学校礼堂,能容纳八百人的场地挤进了近一千二百人,走廊和门口都站满了学生。糖糖作为主讲嘉宾登台时,全场起立鼓掌。
她没有穿华丽的演出服,只是一件白色衬衫配黑色长裤,像极了当年那个蹲在厕所哭的女孩,却又完全不同。
“我曾经觉得,我的人生早就被写好了剧本。”她站在聚光灯下,声音平稳却不失力量,“出生在小县城,父母离异,高中辍学,为了活下去做过很多别人看不起的工作。那时候我觉得,只要能吃饱饭、不被欺负,就是最好的日子。”
台下许多人默默点头。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唱歌?我不是没有梦想,我只是不敢提。因为每次我说我想当歌手,别人就会笑:‘你?省省吧,别做梦了。’”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人群:“但现在我想告诉你们??**你可以做梦,只要你愿意为它流汗。**”
接着,她讲述了自己如何每天凌晨五点起床练声,如何在客户按摩间隙背歌词,如何在被人辱骂时咬牙忍住泪水,只为守住心中那一丝不甘。
“我不是天才,也没有后台。我只是不肯认命。”
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微微发颤:“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和我一样,出身普通,甚至背负污名。但请记住,**你的过去不能定义你,只有你的行动才能。**”
话音落下,掌声如雷。
一名女生冲上台,哽咽着说:“糖糖姐,我也是从酒吧出来的,现在在学校被人叫‘坐台妹’……我一直想退学,觉得自己不配读书。但听了你的话,我不想逃了。我想试试,能不能也活出个人样。”
糖糖抱住她,轻声说:“你会的,一定会的。”
那一晚,主办方收到三百二十七封听众来信,大多是女孩写的。她们诉说着相似的困境:家庭重男轻女、被迫早婚、职场歧视、自我否定……但在信的结尾,几乎都写着同一句话:“我想重新开始。”
回到城市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一位退休教师,住在西北一个小县城。“我七十岁了,一辈子教语文。昨晚看了你们演讲的录像,哭了很久。我有个孙女,十六岁,父母车祸去世,靠亲戚接济生活。她成绩很好,但明年高考后打算放弃学业去打工。我现在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办法让她参加你们的心理辅导课程?费用我可以慢慢付。”
我当即答应,并安排团队开通远程支持通道。
挂掉电话后,我坐在办公桌前,盯着天花板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