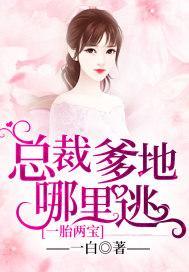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按摩师的自我修养 > 第150章 他们想干什么(第2页)
第150章 他们想干什么(第2页)
那天李奶奶走了,家属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手暖心更暖”。而他在更衣室哭了十分钟,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母亲临终前,也是这样握着他的手,叫错了名字。
“我答应。”他说。
林主任露出一丝笑意,递上笔:“签吧。顺便提醒你一句??别拍照,别录音,别对外透露任何细节。这些人背后牵扯的历史太复杂,有些档案至今未解封。”
老沈签下名字,抬头问:“我能带工具箱去吗?”
“当然。”林主任说,“而且建议你带上艾灸条、火罐、加热垫,甚至可以考虑背个小型中药熏蒸仪。条件艰苦,但我们不想让他们受罪。”
第二天清晨七点,老沈背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出现在XX胡同口。
这里已经被围挡圈了起来,唯一入口处搭了个蓝色铁皮房,挂着“棚改健康服务站”的牌子。门口站着两名穿制服的保安,看到他出示证件后才放行。
胡同狭窄曲折,青砖墙斑驳脱落,电线如蛛网般横跨头顶。不少门楣上还贴着褪色的春联,有的窗户用塑料布封着,风吹时哗啦作响。
第一个上门的是位姓王的老伯,九十二岁,曾是热力管道焊接工。他坐在一把吱呀作响的藤椅上,双腿裹着厚厚的毛毯,膝盖处明显变形。
“疼啊……”老人一开口就是浓重的河北口音,“冬天一到,骨头像被钉子扎着,夜里翻个身都得嚎两嗓子。”
老沈蹲下身,轻轻掀开毯子,触手的一瞬间就明白了??肌肉萎缩严重,皮下组织僵硬如板,膝关节积液明显,但皮肤表面毫无红肿,说明炎症反应早已转入慢性期。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红外测温仪扫了一下,左膝比右膝低了近两度。
“寒痹。”他心里有了数。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用了三段式松解法:先以掌根揉开股四头肌紧张带,再用拇指深压足三里、阳陵泉等穴位激发气血流动,最后以艾灸盒温熨整个膝区。过程中不断询问感受,调整力度。
老人渐渐放松下来,眼皮开始打架。
“你这手法……”他迷迷糊糊地说,“跟我当年在工地看病的军医有点像。”
“哪位军医?”老沈轻声问。
“姓赵……记不清全名了,大家都叫他赵大夫。后来听说转业去了按摩医院……再后来,好像出了什么事,就被调走了。”
老沈手下一顿。
赵大夫?赵大锤?
他不敢深想。
当天下午,他又走访了三位老人。每一位的身体状况都令人揪心:肺纤维化伴肩颈强直、腰椎压缩性骨折未规范治疗、长期便秘引发自主神经紊乱……这些病症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往往被归为“老年共病”,治疗优先级排得很低。但在老沈看来,它们都是可以缓解的。
傍晚六点多,他正准备收工,突然接到林主任电话。
“马上来服务站,紧急情况。”
老沈赶到时,发现屋里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穿白大褂的医生,另一个是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胸前挂着“市档案局”的工作牌。
“这位是陈工,”林主任介绍,“他是负责整理这批老人技术档案的工程师。刚刚他在翻阅一份1958年的地下管网施工记录时,发现了一个异常。”
她把一张泛黄的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上是一群穿着棉袄的工人站在坑道口合影,背景写着“京北一号战备工程竣工留念”。而在人群边缘,有个戴口罩的男人正在记录数据,虽然面目模糊,但右手虎口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
“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张赵大锤年轻时的照片。”陈工说,“根据档案记载,他是该项目的现场医疗保障负责人,擅长用传统疗法处理冻伤和劳损。但他真正的身份,可能不止于此。”
老沈盯着照片,心跳加快。
“我们在另一份绝密文件残页上发现了这个名字。”陈工翻开笔记本,念道:“代号‘铁脊梁’,隶属特别工业支援小组,职责为维持高危岗位人员持续作战能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针灸刺激中枢神经、穴位注射提神药剂、极限状态下的疼痛屏蔽技术……”
屋内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