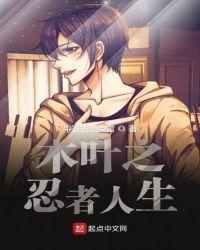笔趣阁>说好当闲散赘婿,你陆地神仙? > 第285章 他这是如何算到的求月票(第1页)
第285章 他这是如何算到的求月票(第1页)
林正弘先是一惊,接着眉头紧锁。
“详细说来。”
“是这样……”
待身着蓝色长衫的粮行主事讲完,林正弘眉头舒缓了一些,语气不满的说:
“几个乞丐的话,可信?”
“哼,我看是。。。
夜深了,学堂里的灯火仍未熄灭。烛火在窗纸上摇曳,映出老师伏案的身影。她正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缓缓写下几个字:“**凡人亦可成光**。”墨迹未干,那片从忆莲飘来的花瓣轻轻落在纸面,竟如活物般沿着笔画游走一圈,随即化作一缕青烟,渗入纸中。整张纸微微发亮,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浸润。
第二天清晨,孩子们来上学时,发现黑板上的“铭记”二字已悄然变为“**共忆**”。
老师没有解释,只是微笑着翻开课本??那已不是官府统编的《圣训要义》,而是一本手抄的《民间纪事》。第一页上写着:
>“本书由三百二十七位守名者口述,经七代人传抄修订而成。不载帝王将相,唯录凡人真事。”
第一课讲的是一个叫陈阿婆的女人。她在饥荒年月里收养了十二个孤儿,自己却饿死在灶台边,临终前还在往锅里放最后一把米。故事末尾附着一句批注:“此名曾被删去三次,今因三人共忆而复现。”
男孩举手问:“她为什么不怕被清纪卫抓走?”
老师停下粉笔,望向窗外湛蓝的天空,“因为她知道,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她做的饭香,她的名字就不会真正消失。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一个人’。”
话音刚落,屋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一名衣衫褴褛的老者拄着竹杖走来,脸上刻满风霜,怀里抱着一卷泛黄的布帛。他站在门口,声音沙哑却清晰:“我走了八百里路,只为送来这个。”
老师认得那布帛的纹样??是西北游侠用来记录亡者名录的“血绢”,以牛皮胶混墨,再蘸死者亲人的血书写,永不褪色。
老者说,他是祁连山下最后一个守碑人。三年前,朝廷派兵欲毁山腰万名人榜,他们以命相护,三十人战死,碑文也被凿去大半。但他连夜背下所有名字,在雪地中爬行七日,将记忆织成这卷血绢。“现在,它该交给你们了。”他说完,盘膝坐地,闭目长眠。
孩子们围上来,轻声念着布帛上的名字。每读出一个,空中便浮起点点微光,如同萤火升腾。当念到“李三娃,七岁,为救同伴坠井”时,教室角落突然响起一声稚嫩的回应:“我在。”
众人回头,只见一个模糊的小影子站在墙角,脸上带着笑,转瞬即逝。
当晚,九处守名圣地同时震动。西湖湖心岛的铜碑自行裂开一道缝,从中涌出无数细小的名字,如蝌蚪游动,汇入地下暗河;敦煌莫高窟内,盲童们集体醒来,齐声背诵一段从未听闻的经文,壁画上的古人竟随之眨眼、点头;北境遗忘谷深处,那道裂缝缓缓张开,一具枯骨缓缓抬起手,指尖在地上划出两个字:**归来**。
与此同时,京城皇宫之中,皇帝独自立于御花园梅树之下。那只曾停驻琉璃瓦檐的火蝶早已不见踪影,但每年清明,它都会回来一次,绕树三圈,然后飞向南方。今年也不例外。
只是这一次,它带回了一封信。
信是用火蝶灰烬与松烟写在桑皮纸上的,字迹潦草却有力:
>“陛下,您还记得东宫西角那棵老槐吗?十年前您亲手埋下的桂花籽,如今已在落槐镇生根发芽。树下坐着一位老人,每日教孩童写字,从不提过往。但他写的第一个字,总是‘苏’。”
>
>“若您愿听一句真言:真正的史书,不在金匮玉册,而在人心深处。
>您可以抹去名字,却抹不去爱;您可以焚尽典籍,却烧不断思念。
>这天下,终究不是谁的天下,而是所有活过之人的天下。”
>
>??阿满
皇帝看完,久久不动。良久,他取下腰间玉佩,轻轻放在梅枝上,低语:“阿琰……回来了。”
次日早朝,皇帝下诏:废除“逆史罪”,赦免所有因言获罪之人,并设立“共忆院”,专司搜集整理民间记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亲自执笔撰写《庶民列传》,首篇便是《忆坊阿满传》。
然而就在诏书颁布当日,南方某村落突发异象。
一座废弃的土地庙中,尘封多年的神龛突然开启,里面并无泥塑金身,只有一面铜镜。镜面原本模糊不清,此刻却渐渐浮现影像:阿满与苏禾并肩坐在昆仑雪山之巅,面前是一条奔腾不息的记忆长河。河水由千万个名字汇聚而成,闪烁如星河倒流。
苏禾轻声道:“源头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