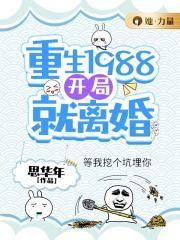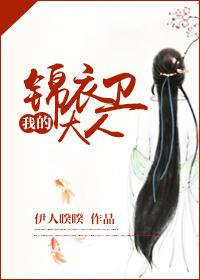笔趣阁>扶苏穿成宋仁宗太子 > 90100(第16页)
90100(第16页)
好戏不能只有一个人来唱,他从善如流地接上:“听这声音……莫非是三元郎?到陛前来说话吧,朕看不见你。”
扶苏:“是。”
他从柱子后绕出来,无比自然地走上中央的大道,一路通向陛前。路上,不知沐浴了多少道意蕴各异的目光。
但扶苏的“自然”,在旁人眼里就成了气度的代名词。寻常人初次登上紫宸殿,谁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行差踏错了一步?谁像他一样昂首挺胸,丝毫不怯场?
赏识他的人颔首点头频频,嫉恨他的人心中暗道“果然是奸臣的苗子”。唯有少数的几个知情人互相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整个皇宫都是他家,有什么怯场的必要?
至于坐在最上首的官家,只有浓浓的老父亲滤镜:儿子怎么看怎么可爱。
“三元郎,你有何事要奏啊?”
语气中不自觉带出点宠孩子的意味,惹得扶苏又挨了许多眼刀。
扶苏被瞪得懵了下,险些忘词。他悄悄咬了下舌头:“臣……臣是来述职的。”
“去岁皇庄的棉花丰收,臣已带着绣娘缝制棉衣有三十七件,手套有五十六件。二旬以前携领国子监、太学学子共著《捧雪集》,雕印凡千三百六十本分发与世人。另著野史怪谈一则,分与二十六说话人,如今,汴京城中无人不知‘棉花’为何物。”
扶苏一口气就是一连串的数据,充分让大宋朝臣理解到了什么叫“可视化”。这不比背骈四俪六轻松多了?
他环视了周围一圈,收获了一堆目瞪口呆后满意地点点头:“官家以为,我这劝农使之职责,履行得如何?”
“当然是……”
“慢着!”忽然有一人跳了出来:“赵小三元,你如何能保证自己说的是真的呢?若是空口无凭胡诌,我也能吹得天花乱坠。”
这人是谁?扶苏不认识。但他在此人的附近看到了悄悄翻了个白眼的司马光。哦,明白了,原来是台谏的人呀——弹劾他的主力军。
扶苏早就预料到有此一遭。不如说,用数据述职是他提前准备好的防打脸装置。他弯了下眼睛,反问道:“那敢问这位大人,庆历五年至今您共上了多少道劾本呢?与同僚们相比,是高还是低?”
那人瞬间不做声了。
若是单问劾本有多少还能随口胡编,谁都不能一时揭穿。但问及和同僚相比?他说高了就是得罪人。说低了就是自己能力不行。
突然却有一道声音横插进来:“不及其同僚远矣。”
司马光说道:“纵是均数,亦远不如。”
那人不可置信地回头,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同僚背刺。但扶苏咬住了下唇,努力不让自己不笑出声来。
“咳咳!”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把话题扭转回自己头上:“你说不出确数,我却能。”
“棉衣手套的数目,都交由户部保管,对不对得上一问便知。”
“《捧雪集》付梓刊印之事是国子监中书局负责,杨祭酒亲手告诉我的数目。”
“汴京的二十四位说话人,更是我亲自托人联系过的。至于汴京城中无人不知‘棉花’……或有夸张之嫌疑,但我走访过汴京十数处街市,问及商贩、闲汉、妇女、孩童共五十人数,他们都说自己听说过棉花。”
“如何,这些可够打消疑虑了?”
扶苏再看那人,已然缩回台谏的队伍里去,脸色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半天却说不出一言。最后只拱了拱手,连句道歉也没说。
唉,一个回合就歇菜了,战斗力不行啊。他还以为能碰到更强力的对手呢。
扶苏假模假样地叹息一声,扫视一周,目光最后移至上首:“官家?可有什么想问的?”
“三元郎不愧是三元郎。”
朕的儿子不愧是朕的儿子。
官家说道:“连履职都让人耳目一新,依朕之见,此法或可推广于众卿家之中。一目了然,不需要旁的虚词了。”
此话一出,朝堂上的人皆抖了三抖。
补药啊官家——
你倒是一目了然了,我们怎么办?!
还是扶苏见势不对,及时解了围:“请官家三思。并非所有政务均可用数字体现。若惹得人急功近利、适得其反就不美。而况数字么,要编一个也很容易的啊。”
台谏的官员队伍中,试图隐身的那人又晃了晃,似有摇摇欲坠之态。所谓“编数字”的反例,现成的不就有一个么?
扶苏:哦豁。
他无辜极了:他是真的误伤。说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个人,有人信吗?
大抵是没人相信了。